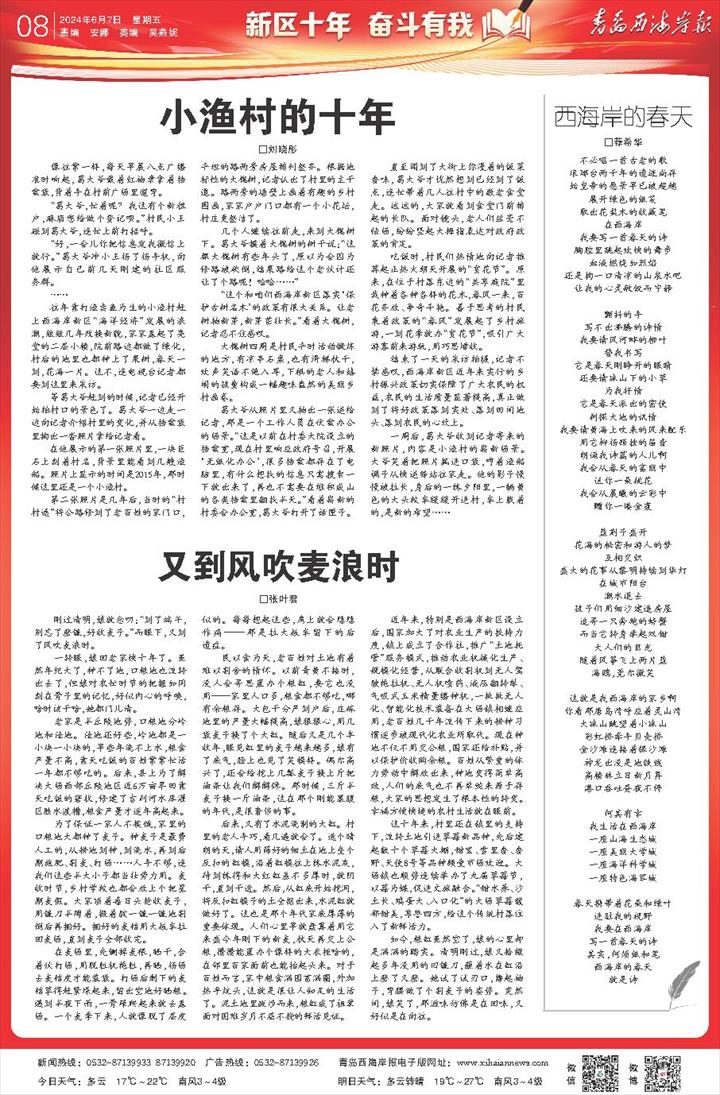文章内容
又到风吹麦浪时
□张叶君
刚过清明,娘就念叨:“到了端午,别忘了磨镰,好收麦子。”而眼下,又到了风吹麦浪时。
一转眼,娘回老家快十年了。虽然年纪大了,种不了地,口粮地也流转出去了,但娘对农忙时节的把握如同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好似内心的呼唤,啥时该干啥,她都门儿清。
老家是半丘陵地势,口粮地分岭地和洼地。洼地还好些,岭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早些年浇不上水,粮食产量不高,靠天吃饭的百姓常常忙活一年都不够吃的。后来,县上为了解决大场西部丘陵地区近6万亩旱田靠天吃饭的窘状,修建了吉利河水库灌区胜水渡槽,粮食产量才逐年高起来。
为了保证一家人不挨饿,家里的口粮地大都种了麦子。种麦子是最费人工的,从耕地到种,到浇水,再到后期施肥、割麦、打场……人手不够,连我们这些半大小子都当壮劳力用。麦收时节,乡村学校也都会放上个把星期麦假。大家顶着毒日头抢收麦子,用镰刀半蹲着,撅着腚一镰一镰地割倒后再捆好。捆好的麦秸用大板车拉回麦场,直到麦子全部收完。
在麦场里,先铡掉麦根,晒干,合着伙打场,用脱粒机拖粒,再晒,扬场去麦秸皮才能装袋。打场后剩下的麦秸草得赶紧垛起来,留出空地好晒粮。遇到半夜下雨,一骨碌爬起来就去盖场。一个麦季下来,人就像脱了层皮似的。每每想起这些,肩上就会隐隐作痛——那是拉大板车留下的后遗症。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前青黄不接时,没人会寻思置办个粮缸,要它也没用——家里人口多,粮食都不够吃,哪有余粮存。大包干分产到户后,庄稼地里的产量大幅提高,娘狠狠心,用几袋麦子换了个大缸。随后又是几个丰收年,眼见缸里的麦子越来越多,娘有了底气,脸上也见了笑模样。偶尔高兴了,还会给挖上几瓢麦子换上斤把油条让我们解解馋。那时候,三斤半麦子换一斤油条,这在那个刚能裹腹的年代,是很奢侈的事。
后来,又有了水泥浇制的大缸。村里的老人手巧,看几遍就会了。选个晴朗的天,请人用筛好的细土在地上垒个反扣的缸模,沿着缸模往上抹水泥灰,待到抹得和大红缸差不多厚时,就阴干,直到干透。然后,从缸底开始挖洞,将反扣缸模子的土全抠出来,水泥缸就做好了。这也是那个年代家底厚薄的重要体现。人们心里早就盘算着用它来盛今年刚下的新麦,秋天再交上公粮,攒攒能置办个像样的大衣柜啥的,在邻里百家面前也能抬起头来。对于百姓而言,家中粮食满囤畜满圈,外加热乎炕头,这就是很让人知足的生活了。泥土地里跋涉而来,粮缸成了祖辈面对困难岁月不屈不挠的鲜活见证。
近年来,特别是西海岸新区设立后,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镇上成立了合作社,推广“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推动农业机械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从联合收割机到无人驾驶拖拉机、无人机喷药、液压翻转犁、气吸式玉米精量播种机,一批批无人化、智能化技术装备在大场镇相继应用,老百姓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耕种习惯逐步被现代化农业所取代。现在种地不仅不用交公粮,国家还给补贴,并以保护价收购余粮。百姓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种地变得简单高效,人们的底气也不再单纯来源于存粮,大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幸福方便快捷的农村生活就在眼前。
这十年来,村里还在镇里的支持下,流转土地引进草莓新品种,先后建起数十个草莓大棚,甜宝、雪里香、香野、天使8号等品种颇受市场欢迎。大场镇也顺势连续举办了九届草莓节,以莓为媒,促进文旅融合。“甜水养、沙土长、鸡蛋大、入口化”的大场草莓馥郁甜美,享誉四方,给这个传统村落注入了新鲜活力。
如今,粮缸虽然空了,娘的心里却是满满的踏实。清明刚过,娘又拾掇起多年没用的旧镰刀,蘸着水在缸沿上磨了又磨。她试了试刃口,撸起袖子,弯腰做了个割麦子的姿势。突然间,娘笑了,那滋味仿佛是在回味,又好似是在向往。
刚过清明,娘就念叨:“到了端午,别忘了磨镰,好收麦子。”而眼下,又到了风吹麦浪时。
一转眼,娘回老家快十年了。虽然年纪大了,种不了地,口粮地也流转出去了,但娘对农忙时节的把握如同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好似内心的呼唤,啥时该干啥,她都门儿清。
老家是半丘陵地势,口粮地分岭地和洼地。洼地还好些,岭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早些年浇不上水,粮食产量不高,靠天吃饭的百姓常常忙活一年都不够吃的。后来,县上为了解决大场西部丘陵地区近6万亩旱田靠天吃饭的窘状,修建了吉利河水库灌区胜水渡槽,粮食产量才逐年高起来。
为了保证一家人不挨饿,家里的口粮地大都种了麦子。种麦子是最费人工的,从耕地到种,到浇水,再到后期施肥、割麦、打场……人手不够,连我们这些半大小子都当壮劳力用。麦收时节,乡村学校也都会放上个把星期麦假。大家顶着毒日头抢收麦子,用镰刀半蹲着,撅着腚一镰一镰地割倒后再捆好。捆好的麦秸用大板车拉回麦场,直到麦子全部收完。
在麦场里,先铡掉麦根,晒干,合着伙打场,用脱粒机拖粒,再晒,扬场去麦秸皮才能装袋。打场后剩下的麦秸草得赶紧垛起来,留出空地好晒粮。遇到半夜下雨,一骨碌爬起来就去盖场。一个麦季下来,人就像脱了层皮似的。每每想起这些,肩上就会隐隐作痛——那是拉大板车留下的后遗症。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前青黄不接时,没人会寻思置办个粮缸,要它也没用——家里人口多,粮食都不够吃,哪有余粮存。大包干分产到户后,庄稼地里的产量大幅提高,娘狠狠心,用几袋麦子换了个大缸。随后又是几个丰收年,眼见缸里的麦子越来越多,娘有了底气,脸上也见了笑模样。偶尔高兴了,还会给挖上几瓢麦子换上斤把油条让我们解解馋。那时候,三斤半麦子换一斤油条,这在那个刚能裹腹的年代,是很奢侈的事。
后来,又有了水泥浇制的大缸。村里的老人手巧,看几遍就会了。选个晴朗的天,请人用筛好的细土在地上垒个反扣的缸模,沿着缸模往上抹水泥灰,待到抹得和大红缸差不多厚时,就阴干,直到干透。然后,从缸底开始挖洞,将反扣缸模子的土全抠出来,水泥缸就做好了。这也是那个年代家底厚薄的重要体现。人们心里早就盘算着用它来盛今年刚下的新麦,秋天再交上公粮,攒攒能置办个像样的大衣柜啥的,在邻里百家面前也能抬起头来。对于百姓而言,家中粮食满囤畜满圈,外加热乎炕头,这就是很让人知足的生活了。泥土地里跋涉而来,粮缸成了祖辈面对困难岁月不屈不挠的鲜活见证。
近年来,特别是西海岸新区设立后,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镇上成立了合作社,推广“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推动农业机械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从联合收割机到无人驾驶拖拉机、无人机喷药、液压翻转犁、气吸式玉米精量播种机,一批批无人化、智能化技术装备在大场镇相继应用,老百姓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耕种习惯逐步被现代化农业所取代。现在种地不仅不用交公粮,国家还给补贴,并以保护价收购余粮。百姓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种地变得简单高效,人们的底气也不再单纯来源于存粮,大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幸福方便快捷的农村生活就在眼前。
这十年来,村里还在镇里的支持下,流转土地引进草莓新品种,先后建起数十个草莓大棚,甜宝、雪里香、香野、天使8号等品种颇受市场欢迎。大场镇也顺势连续举办了九届草莓节,以莓为媒,促进文旅融合。“甜水养、沙土长、鸡蛋大、入口化”的大场草莓馥郁甜美,享誉四方,给这个传统村落注入了新鲜活力。
如今,粮缸虽然空了,娘的心里却是满满的踏实。清明刚过,娘又拾掇起多年没用的旧镰刀,蘸着水在缸沿上磨了又磨。她试了试刃口,撸起袖子,弯腰做了个割麦子的姿势。突然间,娘笑了,那滋味仿佛是在回味,又好似是在向往。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