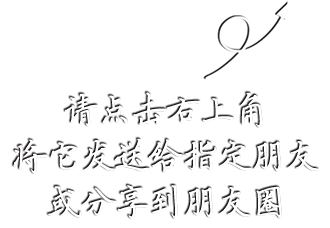夜幕中的挖蛤盛会
青岛西海岸报
2023年09月22日
□刘润清
在大珠山南部的西面,有一个典型的海湾——古镇口湾,它的面积不大,只有19平方公里。由于海湾缩口圆肚的特殊形状,成了船只躲风避浪的天然良港。海滩淤泥淤沙长期沉积,让众多营养物质也在此蓄积,于是这里成为蛤蜊、蛏子、海螺等贝类理想的栖息家园,也成为人们赶海挖蛤的上佳去处。每当大退潮,人们趋之若鹜,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海滩。
每月的初一到初三、十五到十八,是大潮时段,尤其是晚上,落潮最大。如今也不需要记那些诸如“初一十五正日海,吃了晌饭晚了海”“二十二三,两面潮干”“八九两面空,初十大明干”等关于潮汐的口诀了,只要手机搜索一下,枯潮时间(潮水退到最低点的时刻)可以精确到分钟。人们根据枯潮时间,把握住枯潮前后各一个多小时的黄金时间段,便可精准赶海。
六月十七,我们开车于晚上十一点到达古镇口海边,老远就看到海滩上灯光闪闪——这是挖蛤人的头灯在亮。我们赶紧带上工具奔向灯光处,加入这挖蛤盛会。
那晚赶海的人比赶大集的人还多,头灯密集,光圈叠交,熙熙攘攘。人们或蹲着,或坐着马扎,还有的携带更高级的“随身坐墩”——一个高约30厘米的塑料圆柱体,被两条松紧带固定在人的屁股上,像一段粗尾巴,一步一颤,可以随时随地坐下,起立时也不需要手提。发明这个装备的人,估计是目睹过赶海盛况受到了启发,产生了灵感。人们各自手握不同的挖蛤工具,有耙齿形的,有锄头形的,更有甚者,直接拆下电风扇的防护罩当筛子——将沙子捧进防护罩,就着海水晃荡几下,漏掉沙子,就能捡出一把蛤蜊!
这里的蛤蜊个头不大,堪比花生米、指甲盖,色泽杂乱,浅黑色居多,不知是为了融入黑色泥沙环境而进化的保护色,还是被黑色泥沙沤成了这个颜色。
挖蛤蜊选点也是有讲究的。要选那些相对坚硬的地方,如果是松软处,必定是被别人挖过了。其次是选择表面水量适中的地方,要根据自己挖蛤的工具和方式而定,挖蛤时可以借助海水冲掉蛤蜊身上的黑泥,露出真容,减少遗漏。
人们挖蛤手段多样,各显神通。我们这样的雏手一般是一手握锄挖沙,一手捡蛤蜊,按部就班。高手则会用“非常手段”。只见一个妇女弯腰撅腚,把面前的沙层一次性翻松约半个平方,而后反复划拉搅动成泥浆状,不少蛤蜊就自动浮出,她用手泼上一些海水,待蛤蜊清晰可见后,麻利地捡拾裸露的蛤蜊。后来她嫌手捡太慢,就将浮出的蛤蜊连同沙子推进塑料箩筐里,荡掉沙子,扔掉壳皮石块等杂质,一次能收获一大捧。这个原理不难理解:沙子与蛤蜊密度差异较大,在重新沉淀过程中,密度大的沙子会把密度小的蛤蜊挤出来。聪明的海鸥也深谙其道,我曾亲眼见过海鸥在有浮水的沙滩上小脚不停地踏步,把脚下的沙子软化后,就有蛤蜊被挤出沙滩,它们随即啄而食之。
似乎男人们对挖蛤蜊这种“小打小闹”不屑一顾,海滩上的挖蛤人多数是妇女。清凉的海风中,柔和的月光下,她们一边“沙沙”地挖着蛤蜊,一边与同伴说笑着。张家长李家短,超市搞活动,猪肉大涨价,姐姐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姑姑家的表弟要结婚了,东扯葫芦西扯瓢。有的从养生角度出发,建议伙伴严格控制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多吃海鲜少吃肉,剥出蛤蜊肉淘净后连汤冰冻储藏,用来包饺子、汆卤子,既美味又保健。从她们的闲谈中可知,这些挖蛤人有的来自附近村庄,有的来自老胶南县城,有的来自开发区,还有的来自西边偏远乡镇——现在几乎家家都有汽车,三五十公里的距离不算远。
不等涨潮,挖蛤人已经眼花腰酸、颈椎麻木,陆续上岸了。我除了收获了半桶蛤蜊,握锄的手上还收获了一枚豆粒大小的水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