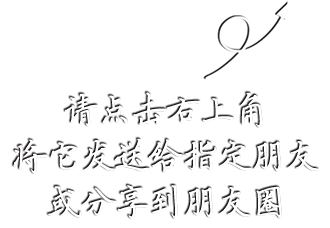儿时的美味
青岛西海岸报
2023年09月22日
□张秀平
大包干以前,农民饭桌上的主食,是地瓜、地瓜面饼子和玉米面饼子,困难时期,玉米面饼子甚至也是奢侈品。记得上小学那会儿,每顿饭全家只热一个玉米面饼子,那是给父亲吃的,因为父亲是家里挑大梁的,母亲、姐姐、妹妹和我,只能吃地瓜或地瓜面饼子。
每年都盼着金秋玉米收获的时节。刚收获的玉米,趁鲜剥下玉米粒,用水磨研磨,在煮地瓜的锅里,烀上一圈鲜玉米面饼子,全家老少便能犒劳一顿。记得母亲蒸熟地瓜和玉米面饼子,打开锅盖,我们围在锅台前,把脖子抻得老长,一股鲜香扑鼻而来——深深吸一口气,让嗅觉先过把瘾!母亲手握锅铲,对准饼子一铲一个,边吹热气,边盛到笸箩里。
还没等母亲端到饭桌上,三只小手已伸进笸箩里,顺手牵饼。因刚出锅,烫手,我们就两只手来回倒弄,口水几乎流到饼子上!母亲边笑边说:“烫手呀,小馋猫们!”我们最喜欢吃的是糊嘠渣儿,又香又甜。狼吞虎咽中,一个玉米面饼子眨眼工夫就进肚了。我们摸着滚圆的肚子,打着饱嗝儿,跑到大街上玩捉迷藏去。
鲜玉米面饼子好吃,磨鲜玉米的过程可并不容易。我和妹妹最怕磨鲜玉米——水磨特别沉,兄妹俩憋足了劲儿,也会在推不到十分钟时就汗流浃背。但为了能吃到美味的玉米面饼子,累也咬牙坚持着。气喘吁吁地休息一会儿,接着再推,等磨完一锅做饼子的玉米,我们已是筋疲力尽!
这真是“饼子好吃,磨难推”啊!
除了鲜玉米面饼子,地瓜面发面饼子也是我的一大“心头好”。每年春天,储藏间的地瓜吃完后,就剩下地瓜干了,上顿地瓜干,下顿还是地瓜干。“如何把地瓜干加工成娃们喜欢吃的饭食?”爱动脑筋的母亲研发了地瓜面发面饼子。先把地瓜干用碓捣碎,再用石磨把半成品研磨成面粉,用箩把面渣筛出来,和面时放一点酵母,和好面饧一会儿。把锅烧热后,两手挖一块,来回颠成团,再用手一拍,把手掌大小的地瓜面饼子轻轻贴到热锅上,“滋啦”冒出一缕热气,盖上锅盖,大火烧开锅,然后小火慢蒸,蒸熟后停火待会儿再开锅,饼子就成了!
在母亲打开锅盖的一刹那,贴在锅上的地瓜面饼子,一个个长成了“小胖猪”,黑中透着亮,亮得发光!母亲把手放到盛满凉水的瓦盆里沾点水,然后迅速把“小胖猪们”拽到笸箩里。我们每人拿一个,捧在手心里软乎乎的,咬一口又松又软,一股特有的甜香顺着食管滑到肚子里,舒服极了!当然天天吃“小胖猪”,也会吃腻。于是,聪慧的母亲就变着花样做饭:用地瓜面玉米面做花卷、地瓜面煎饼、地瓜面包子、地瓜面咸饭……母亲简直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美食家!
在那个缺吃短穿的年代,是母亲用勤劳的双手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的,不只是香甜的饼子,还有母亲那种不畏艰辛、勇于创新的精神。如今时常与朋友在农家宴特色饭馆聚餐,可再难吃出从前的味道。
儿时的美味,永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