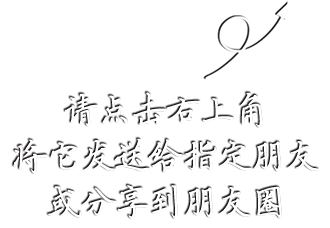看分的日子
青岛西海岸报
2024年08月02日
□刘胜本
那是1985年盛夏的一天。
一大早,我就借了邻居家的大金鹿自行车,去十公里外的母校——胶南二中,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宣判。也许是因为一夜未眠,一路上我无精打采。
看门的大爷一改往日的严肃,笑眯眯地让我进门。校园里冷冷清清,没有了平日的朗朗书声。老师们都还没到,教学楼大门紧锁,被初升的太阳晒得懒洋洋的,宣传栏里悬挂的还是放假前的内容。操场上长满了或高或矮的草,几只知了开始鸣叫八月的烦躁了。突然感觉高中三年朝夕相处的母校一下子陌生了许多。
好在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多,大家满怀心事地相互打过招呼,然后一堆一簇地聚在树荫下、楼墙根,叽叽喳喳起来。
在期望又担心的矛盾心态中,大家一直捱到了11点多,发榜的孙老师才从办公楼里走出,手里捏了一摞纸条站到台阶最高处。“呼啦”一下,三百多个学生将孙老师围了个水泄不通。
孙老师首先公布了理科高考录取分数线:490分,然后按班级里由低到高的分数宣读:“××,390;××,401……”
没注意到别人是何表情,我只觉自己的心跳得厉害,口干舌燥,干咽了几口唾沫。默默祈祷孙老师晚些、再晚些念到自己的名字,却又按捺不住想知道分数的心情。
几个同学悄悄从人群中退出,甚至抹了把眼泪,骑车走了。
“于光荣,491……”
我轻吁一口气,像病人被告知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光荣491分,那就代表还没有念到名字的我肯定过了录取线——前提是孙老师没有将属于我的那张纸条遗漏。
“刘胜本,520。”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那颗高悬的心咕咚一下落回原处。我长吁一口气,为11年的寒窗苦读呼出了一个句号。不,一个叹号!
作别母校,极度的兴奋和喜悦驱赶了饥饿,路旁的知了在齐声祝贺:考上了!考上了!似火的骄阳透过树冠洒下斑斑点点,使单调的道路丰富多彩起来。走了三年的凹凸不平的路似乎一下子平坦了许多,陌生的路人仿佛也在向我投射羡慕的目光。
下午两点,一家人围坐在大门楼下,餐桌早就置好,饭菜也已凉透。父亲在“吧嗒”着旱烟,脚跟处已积满一大堆烟灰;母亲在摇着蒲扇,边为自己扇风,边驱赶饭桌上的苍蝇;为了让我上高中而中途退学并经常为我送饭的姐姐正手捧闲书像是在翻看……而我的位置,早备好了一个马扎。
听到我停放自行车的声音,几个人同时止住了所有动作,齐刷刷地将目光射向我。
“考上了。”我故作平静地说。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下子舒展开紧锁的眉头,狠劲磕掉了刚点燃的旱烟,说了声:“吃饭。”
母亲扔掉蒲扇,赶忙为我盛饭。
姐姐合上书,眼睛分明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