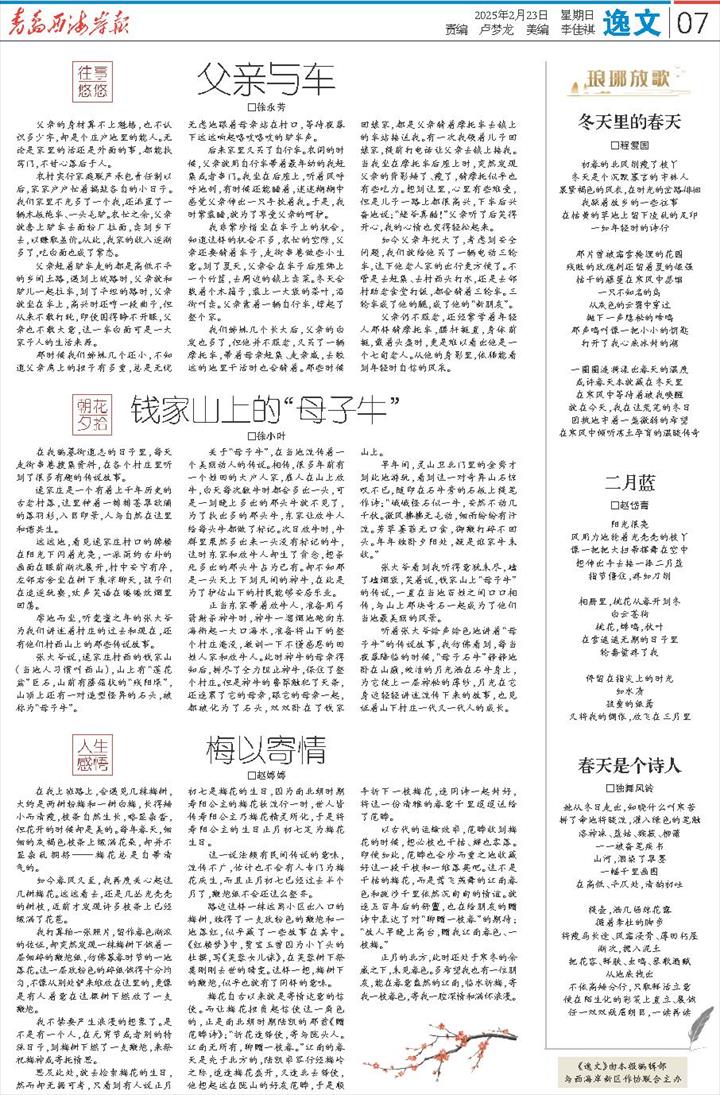文章内容
梅以寄情
□赵婷婷
在我上班路上,会遇见几株梅树,大约是两树粉梅和一树白梅,长得矮小而清瘦,枝条自然生长,略显杂沓,但花开的时候却是美的。每年春天,细细的灰褐色枝条上缀满花朵,却并不显杂乱拥挤——梅花总是自带清气的。
如今春风又至,我再度关心起这几树梅花。远远看去,还是几丛光秃秃的树枝,近前才发现许多枝条上已经缀满了花苞。
我打算拍一张照片,留作春色渐浓的佐证,却突然发现一株梅树下铺着一层细碎的鞭炮纸,仿佛暮春时节的一地落花。这一层玫粉色的碎纸铺得十分均匀,不像从别处铲来堆放在这里的,更像是有人着意在这棵树下燃放了一支鞭炮。
我不禁要产生浪漫的想象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在元宵节或者别的特殊日子,到梅树下燃了一支鞭炮,来祭祀梅神或寄托情思。
思及此处,就去检索梅花的生日,然而却无据可考,只看到有人说正月初七是梅花的生日,因为南北朝时期寿阳公主的梅花妆流行一时,世人皆传寿阳公主乃梅花精灵所化,于是将寿阳公主的生日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生日。
这一说法颇有民间传说的意味,流传不广,估计也不会有人专门为梅花庆生,而且正月初七已经过去半个月了,鞭炮纸不会还这么整齐。
路边这样一株远离小区出入口的梅树,独得了一支玫粉色的鞭炮和一地落红,似乎藏了一些故事在其中。《红楼梦》中,贾宝玉曾因为小丫头的杜撰,写《芙蓉女儿诔》,在芙蓉树下祭奠刚刚去世的晴雯。这样一想,梅树下的鞭炮,似乎也就有了同样的意味。
梅花自古以来就是寄情达意的信使。而让梅花担负起信使这一角色的,正是南北朝时期陆凯的那首《赠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江南的春天是先于北方的,陆凯率军行经梅岭之际,适逢梅花盛开,又逢北去驿使,他想起远在陇山的好友范晔,于是顺手折下一枝梅花,连同诗一起封好,将这一份清雅的春意千里迢迢送给了范晔。
以古代的运输效率,范晔收到梅花的时候,想必枝也干枯、瓣也零落。即便如此,范晔也会珍而重之地收藏好这一段干枝和一堆落英吧。这不是干枯的梅花,而是莺飞燕舞的江南春色和跋涉千里依然沉甸甸的情谊。就连五百年后的舒亶,也在给朋友的赠诗中表达了对“聊赠一枝春”的期待:“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正月的北方,此时还处于寒冬的余威之下,未见春色。多希望我也有一位朋友,能在春意盎然的江南,临水折梅,寄我一枝春色,寄我一腔深情和满怀浪漫。
在我上班路上,会遇见几株梅树,大约是两树粉梅和一树白梅,长得矮小而清瘦,枝条自然生长,略显杂沓,但花开的时候却是美的。每年春天,细细的灰褐色枝条上缀满花朵,却并不显杂乱拥挤——梅花总是自带清气的。
如今春风又至,我再度关心起这几树梅花。远远看去,还是几丛光秃秃的树枝,近前才发现许多枝条上已经缀满了花苞。
我打算拍一张照片,留作春色渐浓的佐证,却突然发现一株梅树下铺着一层细碎的鞭炮纸,仿佛暮春时节的一地落花。这一层玫粉色的碎纸铺得十分均匀,不像从别处铲来堆放在这里的,更像是有人着意在这棵树下燃放了一支鞭炮。
我不禁要产生浪漫的想象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在元宵节或者别的特殊日子,到梅树下燃了一支鞭炮,来祭祀梅神或寄托情思。
思及此处,就去检索梅花的生日,然而却无据可考,只看到有人说正月初七是梅花的生日,因为南北朝时期寿阳公主的梅花妆流行一时,世人皆传寿阳公主乃梅花精灵所化,于是将寿阳公主的生日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生日。
这一说法颇有民间传说的意味,流传不广,估计也不会有人专门为梅花庆生,而且正月初七已经过去半个月了,鞭炮纸不会还这么整齐。
路边这样一株远离小区出入口的梅树,独得了一支玫粉色的鞭炮和一地落红,似乎藏了一些故事在其中。《红楼梦》中,贾宝玉曾因为小丫头的杜撰,写《芙蓉女儿诔》,在芙蓉树下祭奠刚刚去世的晴雯。这样一想,梅树下的鞭炮,似乎也就有了同样的意味。
梅花自古以来就是寄情达意的信使。而让梅花担负起信使这一角色的,正是南北朝时期陆凯的那首《赠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江南的春天是先于北方的,陆凯率军行经梅岭之际,适逢梅花盛开,又逢北去驿使,他想起远在陇山的好友范晔,于是顺手折下一枝梅花,连同诗一起封好,将这一份清雅的春意千里迢迢送给了范晔。
以古代的运输效率,范晔收到梅花的时候,想必枝也干枯、瓣也零落。即便如此,范晔也会珍而重之地收藏好这一段干枝和一堆落英吧。这不是干枯的梅花,而是莺飞燕舞的江南春色和跋涉千里依然沉甸甸的情谊。就连五百年后的舒亶,也在给朋友的赠诗中表达了对“聊赠一枝春”的期待:“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正月的北方,此时还处于寒冬的余威之下,未见春色。多希望我也有一位朋友,能在春意盎然的江南,临水折梅,寄我一枝春色,寄我一腔深情和满怀浪漫。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