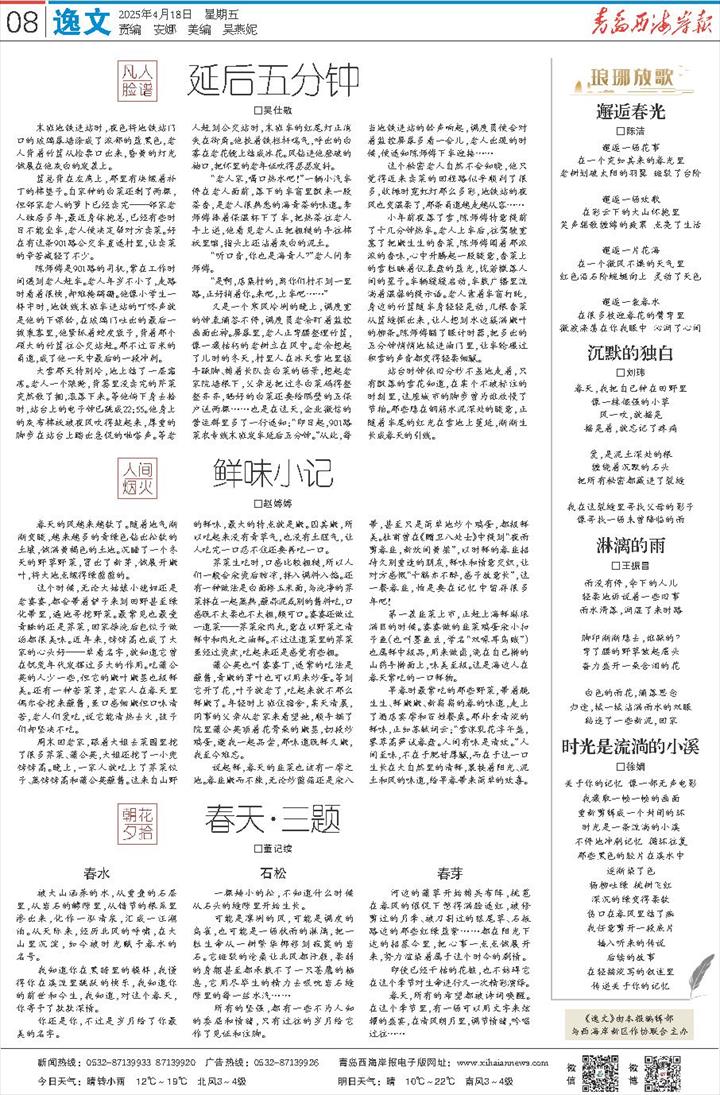文章内容
鲜味小记
□赵婷婷
春天的风越来越软了。随着地气渐渐变暖,越来越多的青绿色钻出松软的土壤,铺满黄褐色的土地。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野草野菜,冒出了新芽,铺展开嫩叶,将大地点缀得绿茵茵的。
这个时候,无论大姑娘小媳妇还是老婆婆,都会带着铲子来到田野甚至绿化带里,遍地寻挖野菜。最常见也最受青睐的还是荠菜,回家择洗后包饺子做汤都很美味。近年来,饽饽蒿也成了大家的心头好——单看名字,就知道它曾在饥荒年代发挥过多大的作用。吃蒲公英的人少一些,但它的嫩叶嫩茎也极鲜美。还有一种苦菜芽,老家人在春天里偶尔会挖来蘸酱,虽口感细嫩但口味清苦,老人们爱吃,说它能清热去火,孩子们却坚决不吃。
周末回老家,跟着大姐去菜园里挖了很多荠菜、蒲公英,大姐还挖了一小兜饽饽蒿。晚上,一家人就吃上了荠菜饺子、蒸饽饽蒿和蒲公英蘸酱。这来自山野的鲜味,最大的特点就是嫩。因其嫩,所以吃起来没有青草气,也没有土腥气,让人吃完一口忍不住还要再吃一口。
荠菜生吃时,口感比较粗糙,所以人们一般会汆烫后晾凉,拌入调料入馅。还有一种做法是白面掺玉米面,与洗净的荠菜拌在一起蒸熟,蘸蒜泥或别的酱料吃,口感既不太柔也不太粗,颇可口。婆婆还做过一道菜——荠菜汆肉丸,意在以野菜之清鲜中和肉丸之油鲜。不过这道菜里的荠菜虽经过烫煮,吃起来还是感觉有些粗。
蒲公英也叫婆婆丁,通常的吃法是蘸酱,青嫩的芽叶也可以用来炒蛋。等到它开了花,叶子就老了,吃起来就不那么鲜嫩了。年轻时上班住宿舍,某天清晨,同事的父亲从老家来看望她,顺手摘了院里蒲公英顶着花骨朵的嫩茎,切段炒鸡蛋,邀我一起品尝,那味道既鲜又嫩,我至今难忘。
说起鲜,春天的韭菜也该有一席之地。春韭嫩而不辣,无论炒菌菇还是汆八带,甚至只是简单地炒个鸡蛋,都极鲜美。杜甫曾在《赠卫八处士》中提到“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以时鲜的春韭招待久别重逢的朋友,鲜味和情意交织,让对方感慨“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一餐春韭,怕是要在记忆中留存很多年吧!
第一茬韭菜上市,正赶上海鲜琳琅满目的时候。婆婆做的韭菜鸡蛋汆小扣子鱼(也叫墨鱼豆,学名“双喙耳乌贼”)也属鲜中极品,用来做卤,浇在自己擀的山药手擀面上,味美至极。这是海边人在春天常吃的一口鲜物。
早春时最常吃的那些野菜,带着脆生生、鲜嫩嫩、新崭崭的春的味道,走上了酒店宴席和百姓餐桌。那朴素清淡的鲜味,正如苏轼词云:“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人间至味,不在于肥甘厚腻,而在于这一口生长在大自然里的清鲜,裹挟着阳光、泥土和风的味道,给早春带来简单的欢喜。
春天的风越来越软了。随着地气渐渐变暖,越来越多的青绿色钻出松软的土壤,铺满黄褐色的土地。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野草野菜,冒出了新芽,铺展开嫩叶,将大地点缀得绿茵茵的。
这个时候,无论大姑娘小媳妇还是老婆婆,都会带着铲子来到田野甚至绿化带里,遍地寻挖野菜。最常见也最受青睐的还是荠菜,回家择洗后包饺子做汤都很美味。近年来,饽饽蒿也成了大家的心头好——单看名字,就知道它曾在饥荒年代发挥过多大的作用。吃蒲公英的人少一些,但它的嫩叶嫩茎也极鲜美。还有一种苦菜芽,老家人在春天里偶尔会挖来蘸酱,虽口感细嫩但口味清苦,老人们爱吃,说它能清热去火,孩子们却坚决不吃。
周末回老家,跟着大姐去菜园里挖了很多荠菜、蒲公英,大姐还挖了一小兜饽饽蒿。晚上,一家人就吃上了荠菜饺子、蒸饽饽蒿和蒲公英蘸酱。这来自山野的鲜味,最大的特点就是嫩。因其嫩,所以吃起来没有青草气,也没有土腥气,让人吃完一口忍不住还要再吃一口。
荠菜生吃时,口感比较粗糙,所以人们一般会汆烫后晾凉,拌入调料入馅。还有一种做法是白面掺玉米面,与洗净的荠菜拌在一起蒸熟,蘸蒜泥或别的酱料吃,口感既不太柔也不太粗,颇可口。婆婆还做过一道菜——荠菜汆肉丸,意在以野菜之清鲜中和肉丸之油鲜。不过这道菜里的荠菜虽经过烫煮,吃起来还是感觉有些粗。
蒲公英也叫婆婆丁,通常的吃法是蘸酱,青嫩的芽叶也可以用来炒蛋。等到它开了花,叶子就老了,吃起来就不那么鲜嫩了。年轻时上班住宿舍,某天清晨,同事的父亲从老家来看望她,顺手摘了院里蒲公英顶着花骨朵的嫩茎,切段炒鸡蛋,邀我一起品尝,那味道既鲜又嫩,我至今难忘。
说起鲜,春天的韭菜也该有一席之地。春韭嫩而不辣,无论炒菌菇还是汆八带,甚至只是简单地炒个鸡蛋,都极鲜美。杜甫曾在《赠卫八处士》中提到“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以时鲜的春韭招待久别重逢的朋友,鲜味和情意交织,让对方感慨“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一餐春韭,怕是要在记忆中留存很多年吧!
第一茬韭菜上市,正赶上海鲜琳琅满目的时候。婆婆做的韭菜鸡蛋汆小扣子鱼(也叫墨鱼豆,学名“双喙耳乌贼”)也属鲜中极品,用来做卤,浇在自己擀的山药手擀面上,味美至极。这是海边人在春天常吃的一口鲜物。
早春时最常吃的那些野菜,带着脆生生、鲜嫩嫩、新崭崭的春的味道,走上了酒店宴席和百姓餐桌。那朴素清淡的鲜味,正如苏轼词云:“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人间至味,不在于肥甘厚腻,而在于这一口生长在大自然里的清鲜,裹挟着阳光、泥土和风的味道,给早春带来简单的欢喜。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