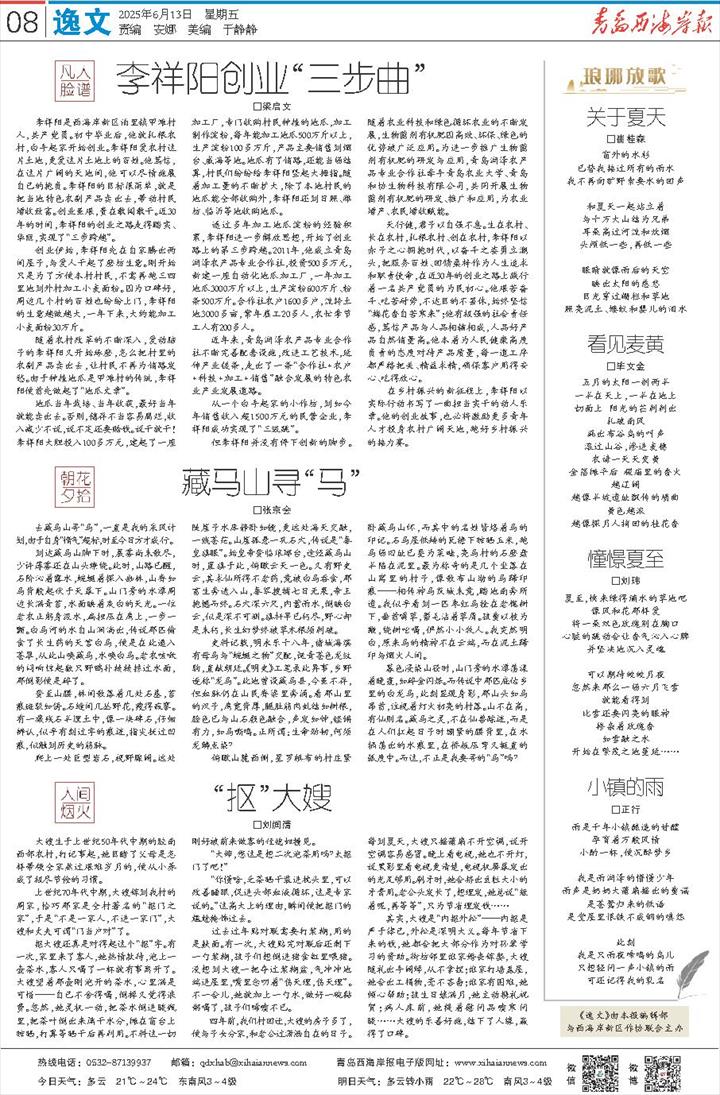文章内容
藏马山寻“马”
□张京会
去藏马山寻“马”,一直是我的采风计划,由于自身“惰气”超标,时至今日方才成行。
到达藏马山脚下时,晨雾尚未散尽,少许薄雾还在山头缭绕。此时,山路已醒,石阶沁着露水,蜿蜒着探入幽林,山脊如马背般起伏于天幕下。山门旁的水潭周边长满青苔,水面映着灰白的天光。一位老农正躬身汲水,扁担压在肩上,一步一颤。白马河的水自山涧淌出,传说那匹偷食了长生药的天宫白马,便是在此遁入苍翠,从此山唤藏马,水唤白马。老农咳嗽的闷响惊起数只野鸭扑棱棱掠过水面,那倒影便是碎了。
登至山腰,林间散落着几处石基,苔痕斑驳如锈。石缝间几丛野花,瘦得寂寥。有一截残石半埋土中,像一块碑石,仔细辨认,似乎有刻过字的痕迹,指尖抚过凹痕,似触到历史的筋脉。
爬上一处巨型岩石,视野骤阔。远处陡崖子水库静卧如镜,更远处海天交融,一线苍茫。山崖孤悬一孔石穴,传说是“秦皇旗眼”。始皇帝登临琅琊台,途经藏马山时,置旗于此,俯瞰云天一色。又有野史云,其求仙所得不老药,竟被白马吞食,那畜生奔逃入山,秦军搜捕七日无果,帝王抱憾而终。石穴深六尺,内蓄雨水,倒映白云,似是深不可测。旗杆早已朽尽,野心却是未朽,长生幻梦终被草木根须刺破。
史料记载,明永乐十八年,诸城海滨有母马与“蜿蜒之物”交配,诞青苍色龙纹驹,直献朝廷。《明史》工笔录此异事,乡野遂称“龙马”。此地曾设藏马县,今虽不存,但血脉仍在山民脊梁里奔涌。看那山里的汉子,肩宽背厚,腿肚筋肉虬结如树根,脸色已与山石颜色融合,声发如钟,铿锵有力,如马嘶鸣。正所谓:生命劲韧,何须龙鳞点染?
俯瞰山麓西侧,星罗棋布的村庄紧卧藏马山怀,而其中的名姓皆烙着马的印记。石马屋低矮的瓦檐下晾晒玉米,跑马场旧址已垦为菜畦,亮马村的石磨盘半陷在泥里。最为称奇的是几个坐落在山窝里的村子,像散布山坳的马蹄印痕——相传神马筑城未竟,踏地南奔所遗。我似乎看到一匹枣红马拴在老槐树下,垂首嚼草,鬃毛沾着草屑。孩童以枝为鞭,绕树吆喝,俨然小小牧人。我突然明白,原来马的精神不在云端,而在泥土蹄印与烟火人间。
暮色浸染山径时,山门旁的水潭荡漾着晚霞,如碎金闪烁。而传说中那匹庇佑乡里的白龙马,此刻显现身影,那山头如马昂首,注视着灯火初亮的村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藏马之灵,不在仙兽踪迹,而是在人们扛起日子时绷紧的腰背里,在水桶荡出的水痕里,在桥板压弯又挺直的弧度中。而这,不正是我要寻的“马”吗?
去藏马山寻“马”,一直是我的采风计划,由于自身“惰气”超标,时至今日方才成行。
到达藏马山脚下时,晨雾尚未散尽,少许薄雾还在山头缭绕。此时,山路已醒,石阶沁着露水,蜿蜒着探入幽林,山脊如马背般起伏于天幕下。山门旁的水潭周边长满青苔,水面映着灰白的天光。一位老农正躬身汲水,扁担压在肩上,一步一颤。白马河的水自山涧淌出,传说那匹偷食了长生药的天宫白马,便是在此遁入苍翠,从此山唤藏马,水唤白马。老农咳嗽的闷响惊起数只野鸭扑棱棱掠过水面,那倒影便是碎了。
登至山腰,林间散落着几处石基,苔痕斑驳如锈。石缝间几丛野花,瘦得寂寥。有一截残石半埋土中,像一块碑石,仔细辨认,似乎有刻过字的痕迹,指尖抚过凹痕,似触到历史的筋脉。
爬上一处巨型岩石,视野骤阔。远处陡崖子水库静卧如镜,更远处海天交融,一线苍茫。山崖孤悬一孔石穴,传说是“秦皇旗眼”。始皇帝登临琅琊台,途经藏马山时,置旗于此,俯瞰云天一色。又有野史云,其求仙所得不老药,竟被白马吞食,那畜生奔逃入山,秦军搜捕七日无果,帝王抱憾而终。石穴深六尺,内蓄雨水,倒映白云,似是深不可测。旗杆早已朽尽,野心却是未朽,长生幻梦终被草木根须刺破。
史料记载,明永乐十八年,诸城海滨有母马与“蜿蜒之物”交配,诞青苍色龙纹驹,直献朝廷。《明史》工笔录此异事,乡野遂称“龙马”。此地曾设藏马县,今虽不存,但血脉仍在山民脊梁里奔涌。看那山里的汉子,肩宽背厚,腿肚筋肉虬结如树根,脸色已与山石颜色融合,声发如钟,铿锵有力,如马嘶鸣。正所谓:生命劲韧,何须龙鳞点染?
俯瞰山麓西侧,星罗棋布的村庄紧卧藏马山怀,而其中的名姓皆烙着马的印记。石马屋低矮的瓦檐下晾晒玉米,跑马场旧址已垦为菜畦,亮马村的石磨盘半陷在泥里。最为称奇的是几个坐落在山窝里的村子,像散布山坳的马蹄印痕——相传神马筑城未竟,踏地南奔所遗。我似乎看到一匹枣红马拴在老槐树下,垂首嚼草,鬃毛沾着草屑。孩童以枝为鞭,绕树吆喝,俨然小小牧人。我突然明白,原来马的精神不在云端,而在泥土蹄印与烟火人间。
暮色浸染山径时,山门旁的水潭荡漾着晚霞,如碎金闪烁。而传说中那匹庇佑乡里的白龙马,此刻显现身影,那山头如马昂首,注视着灯火初亮的村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藏马之灵,不在仙兽踪迹,而是在人们扛起日子时绷紧的腰背里,在水桶荡出的水痕里,在桥板压弯又挺直的弧度中。而这,不正是我要寻的“马”吗?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