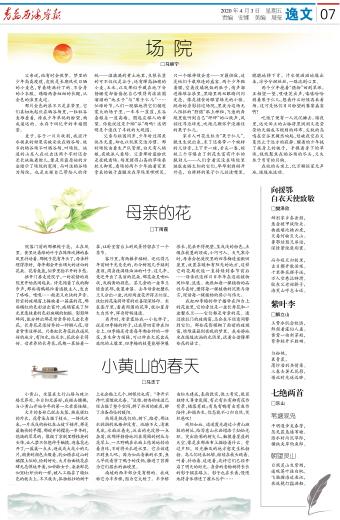场 院
□马婉宁
父亲说,他有时会做梦。梦里的少年高高瘦瘦,皮肤是长期风吹日晒的小麦色,穿着缝满补丁的、不合身的小衣服,踢踏两条细细的长腿,从金色的浪里走过。
那片金色的浪不只是在梦里。它们真切地起伏在晒谷场里,一粒粒谷麦堆叠着,排成少年单纯的盼望,构成遥远的、永存于回忆中的幸福图景。
麦子、谷子一片片收割,咸涩汗水换来的甜果实被安放在晒谷场。故乡的晒谷场不叫晒谷场,叫场院。地道的山东人在吐出这两个字时还会长长地拖着腔儿,像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暗示了场院的宽阔。而叫这晒谷场为场院,也是庄稼自己带给人的传统——湿漉漉的黄土地里,生根长茎的可不仅仅是谷子,还有蹿高抽穗的小麦、玉米,以及那似乎藏在地下安静睡觉却偷偷把自己喂得肉滚滚圆溜溜的“地豆子”与“果子仁儿”……忙碌时节,人们一股脑地将它们铺进宽大的场子里,一车车一筐筐,五谷杂粮垒一道高墙,围起庄稼人的希望。你能说这是个晒“谷”场吗?这明明是个逮住了丰收的大观园。
父亲与祖国同岁,少年时过得虽快乐无虞,却也以饥寒交迫为惯。那时场院由着生产队管理,白天有人晒粮,夜晚派人看场。父亲那时最盼就是夜晚看场。场里摞得山高的草垛柔软又御寒,看场的两个少年抱着家里拿来的被子盘腿坐在草垛里嘿嘿笑,只一个眼神便会意——万籁俱寂,这是他们千载难逢的盛宴。两个少年猫着腰,空着没填晚饭的肚子,悄声溜进粮堆谷浪里,黑暗里两双眼睛闪闪发亮,像是捕食时眼冒绿光的小狼。跳动的身影掠过场院,黑夜为这场无人阻拦的“狩猎”添上神秘,飞速的奔跑里能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风掠过耳边碎发,吹跑几颗怀中没搂住的果子仁儿。
家乡人叫花生粒为“果子仁儿”,脆生生说出来,末了还要带一个婉转的儿话音,上下牙一碰,舌尖一卷,短短三个字爆出了新花生富有汁水的脆劲儿——人们拿着还没在场院里挺肚皮晒太阳的它们,毕毕剥剥掰开外壳,白胖胖的果子仁儿放进嘴里,脆脆地弹下牙,汁水便滋滋地爆出来,凉兮兮甜丝丝,一路流到心里。
两个少年抱着“猎物”回到草垛,互相望一望,噗嗤笑出声,嘻嘻哈哈剥着果子仁儿,想着什么时候再来看场。这可是他们日日盼望的饕餮盛宴啊!
吃饱了便有一人沉沉睡去。暗夜里,远处耸立的山脉将黑洞洞又亮莹莹的天锯成不规则的碎布。尖锐的鸟鸣在空谷里骤然响起,划破夜空后又戛然止于远方的寂静。醒着的少年拢了拢身上的被子,手摸着身下的草垛,视线聚焦在晒谷场的尽头,又失焦于弯弯的月钩。
在他的头顶上,亿万颗恒星无声地、缓缓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