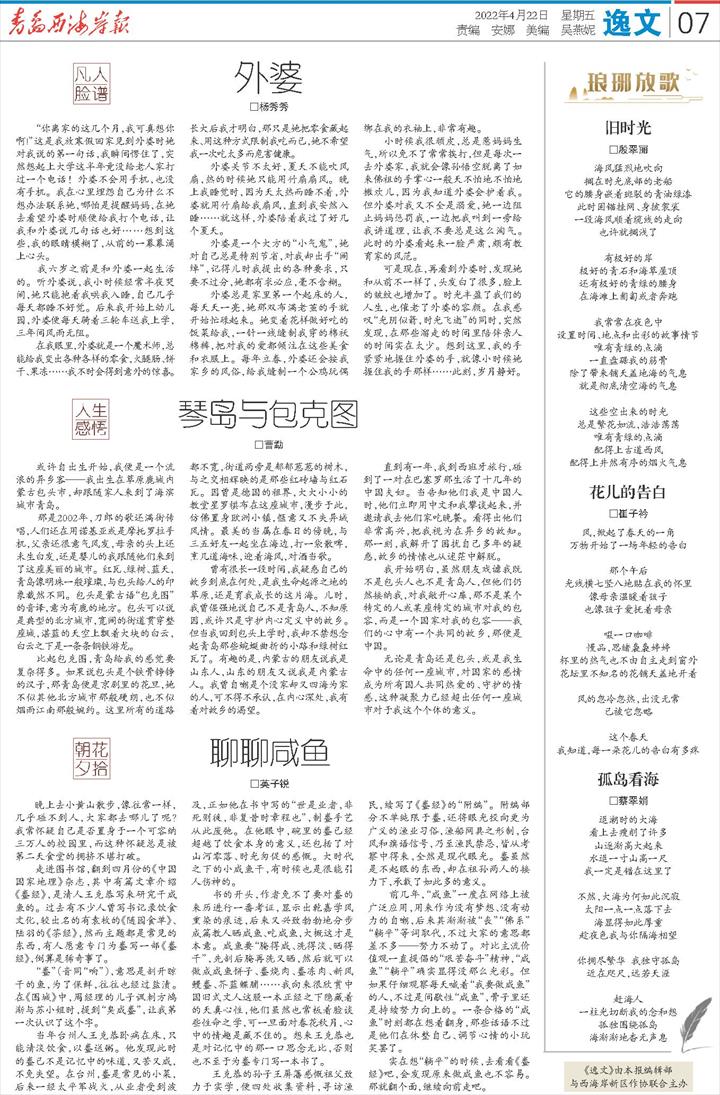文章内容
朝花夕拾
聊聊咸鱼
□英子锐
晚上去小黄山散步,像往常一样,几乎碰不到人,大家都去哪儿了呢?我常怀疑自己是否置身于一个可容纳三万人的校园里,而这种怀疑总是被第二天食堂的拥挤不堪打破。
走进图书馆,翻到四月份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其中有篇文章介绍《鲞经》,是清人王克恭写来研究干咸鱼的。过去有不少人曾写书记录饮食文化,较出名的有袁枚的《随园食单》、陆羽的《茶经》,然而主题都是常见的东西,有人愿意专门为鲞写一部《鲞经》,倒算是稀奇事了。
“鲞”(音同“响”),意思是剖开晾干的鱼,为了保鲜,往往也经过盐渍。在《围城》中,周经理的儿子讽刺方鸿渐与苏小姐时,提到“臭咸鲞”,让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字。
当年台州人王克恭卧病在床,只能清淡饮食,以鲞送粥。他发现此时的鲞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又苦又咸,不免失望。在台州,鲞是常见的小菜,后来一经太平军战火,从业者受到波及,正如他在书中写的“世是业者,非死则徙,非复昔时章程也”,制鲞手艺从此废弛。在他眼中,碗里的鲞已经超越了饮食本身的意义,还包括了对山河零落、时光匆促的感慨。大时代之下的小咸鱼干,有时候也是很能引人伤神的。
书的开头,作者免不了要对鲞的来历进行一番考证,显示出乾嘉学风熏染的痕迹,后来又兴致勃勃地分步成篇教人晒咸鱼、吃咸鱼,大概这才是本意。咸鱼要“腌得咸、洗得淡、晒得干”,先剖后腌再洗又晒,然后就可以做成咸鱼饼子、鲞烧肉、鲞冻肉、新风鳗鲞、芥蓝鲽脯……我向来很欣赏中国旧式文人这股一本正经之下隐藏着的天真心性,他们虽然也常板着脸谈些性命之学,可一旦面对春花秋月,心中的情趣是藏不住的。想来王克恭也是对记忆中的那一口思念无比,否则也不至于为鲞专门写一本书了。
王克恭的孙子王屏藩感慨祖父致力于实学,便四处收集资料,寻访渔民,续写了《鲞经》的“附编”。附编部分不单纯限于鲞,还将眼光投向更为广义的渔业习俗,渔船网具之形制,台风和旗语信号,乃至渔民禁忌,皆从考察中得来,全然是现代眼光。鲞虽然是不起眼的东西,却在祖孙两人的接力下,承载了如此多的意义。
前几年,“咸鱼”一度在网络上被广泛应用,用来作为没有梦想、没有动力的自嘲,后来其渐渐被“丧”“佛系”“躺平”等词取代,不过大家的意思都差不多——努力不动了。对比主流价值观一直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咸鱼”“躺平”确实显得没那么光彩。但如果仔细观察每天喊着“我要做咸鱼”的人,不过是间歇性“咸鱼”,骨子里还是持续努力向上的。一条合格的“咸鱼”时刻都在想着翻身,那些话语不过是他们在休整自己、调节心情的小玩笑罢了。
实在想“躺平”的时候,去看看《鲞经》吧,会发现原来做咸鱼也不容易。那就翻个面,继续向前走吧。
晚上去小黄山散步,像往常一样,几乎碰不到人,大家都去哪儿了呢?我常怀疑自己是否置身于一个可容纳三万人的校园里,而这种怀疑总是被第二天食堂的拥挤不堪打破。
走进图书馆,翻到四月份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其中有篇文章介绍《鲞经》,是清人王克恭写来研究干咸鱼的。过去有不少人曾写书记录饮食文化,较出名的有袁枚的《随园食单》、陆羽的《茶经》,然而主题都是常见的东西,有人愿意专门为鲞写一部《鲞经》,倒算是稀奇事了。
“鲞”(音同“响”),意思是剖开晾干的鱼,为了保鲜,往往也经过盐渍。在《围城》中,周经理的儿子讽刺方鸿渐与苏小姐时,提到“臭咸鲞”,让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字。
当年台州人王克恭卧病在床,只能清淡饮食,以鲞送粥。他发现此时的鲞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又苦又咸,不免失望。在台州,鲞是常见的小菜,后来一经太平军战火,从业者受到波及,正如他在书中写的“世是业者,非死则徙,非复昔时章程也”,制鲞手艺从此废弛。在他眼中,碗里的鲞已经超越了饮食本身的意义,还包括了对山河零落、时光匆促的感慨。大时代之下的小咸鱼干,有时候也是很能引人伤神的。
书的开头,作者免不了要对鲞的来历进行一番考证,显示出乾嘉学风熏染的痕迹,后来又兴致勃勃地分步成篇教人晒咸鱼、吃咸鱼,大概这才是本意。咸鱼要“腌得咸、洗得淡、晒得干”,先剖后腌再洗又晒,然后就可以做成咸鱼饼子、鲞烧肉、鲞冻肉、新风鳗鲞、芥蓝鲽脯……我向来很欣赏中国旧式文人这股一本正经之下隐藏着的天真心性,他们虽然也常板着脸谈些性命之学,可一旦面对春花秋月,心中的情趣是藏不住的。想来王克恭也是对记忆中的那一口思念无比,否则也不至于为鲞专门写一本书了。
王克恭的孙子王屏藩感慨祖父致力于实学,便四处收集资料,寻访渔民,续写了《鲞经》的“附编”。附编部分不单纯限于鲞,还将眼光投向更为广义的渔业习俗,渔船网具之形制,台风和旗语信号,乃至渔民禁忌,皆从考察中得来,全然是现代眼光。鲞虽然是不起眼的东西,却在祖孙两人的接力下,承载了如此多的意义。
前几年,“咸鱼”一度在网络上被广泛应用,用来作为没有梦想、没有动力的自嘲,后来其渐渐被“丧”“佛系”“躺平”等词取代,不过大家的意思都差不多——努力不动了。对比主流价值观一直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咸鱼”“躺平”确实显得没那么光彩。但如果仔细观察每天喊着“我要做咸鱼”的人,不过是间歇性“咸鱼”,骨子里还是持续努力向上的。一条合格的“咸鱼”时刻都在想着翻身,那些话语不过是他们在休整自己、调节心情的小玩笑罢了。
实在想“躺平”的时候,去看看《鲞经》吧,会发现原来做咸鱼也不容易。那就翻个面,继续向前走吧。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