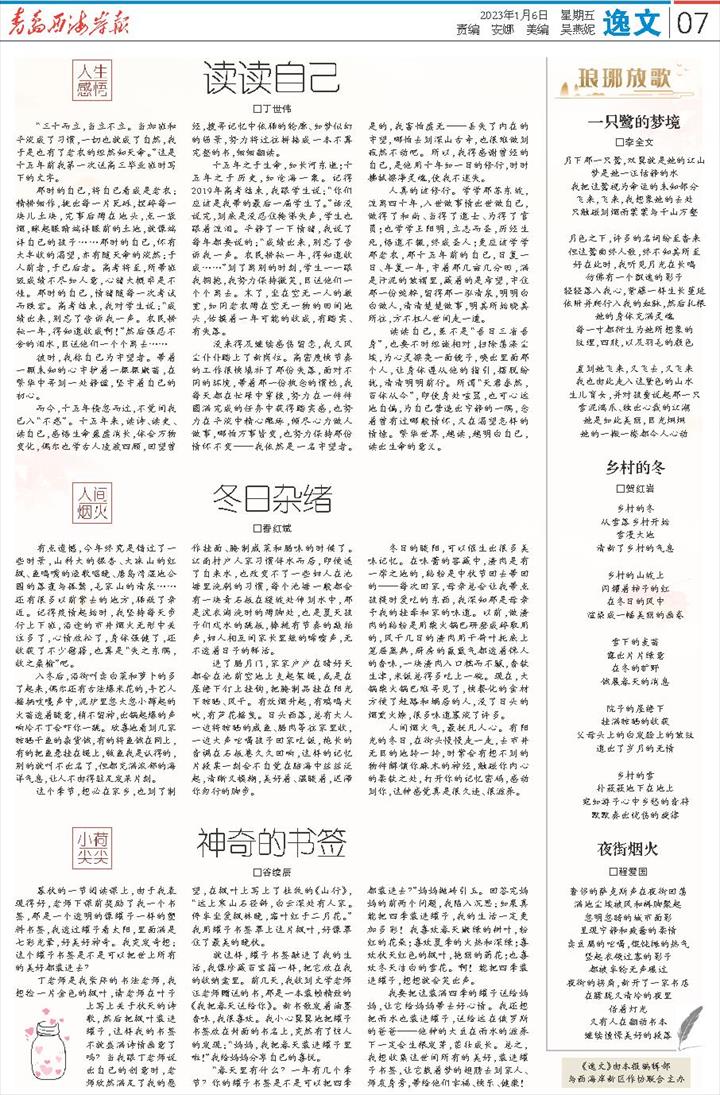文章内容
冬日杂绪
□香红斌
有点遗憾,今年终究是错过了一些时景,山科大的银杏、大珠山的红枫、鱼鸣嘴的渔歌唱晚、唐岛湾湿地公园的落霞与孤鹜,毛家山的清泉……还有很多以前常去的地方,稀疏了亲近。记得疫情起始时,我坚持每天步行上下班,沿途的市井烟火无形中关注多了,心情放松了,身体强健了,还收获了不少慰藉,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入冬后,沿街叫卖白菜和萝卜的多了起来,偶尔还有古法爆米花的,手艺人摇柄吱嘎声中,泥炉里忽大忽小蹿起的火苗透着暖意,稍不留神,出锅起爆的声响冷不丁会吓你一跳。欣喜地看到几家晾晒干鱼的杂货铺,有的将鱼铺在网上,有的把鱼悬挂在绳上,鲅鱼我是认得的,别的就叫不出名了,但都充满浓郁的海洋气息,让人不由得驻足发呆片刻。
这个季节,想必在家乡,也到了制作挂面、腌制咸菜和腊味的时候了。江南村户人家习惯伴水而居,即便通了自来水,也改变不了一些妇人在池塘里洗刷的习惯,每个池塘一般都会有一块青石板在缓坡处伸到水中,那是浣衣淘洗时的蹲脚处,也是夏天孩子们戏水的跳板,棒槌有节奏的敲拍声,妇人相互间家长里短的唏嘘声,无不透着日子的鲜活。
进了腊月门,家家户户在晴好天都会在池前空地上支起架绳,或是在屋檐下钉上挂钩,把腌制品挂在阳光下晾晒、风干。有炊烟升起,有鸡鸣犬吠,有芦花摇曳。日头西落,总有大人一边将晾晒的咸鱼、腊肉等往家里收,一边大声吆喝孩子回家吃饭,拖长的音调在石板巷久久回响,这样的记忆片段某一刻会不自觉在脑海中丝丝泛起,清晰又模糊,美好着、温暖着,迟滞你匆行的脚步。
冬日的暖阳,可以催生出很多美味记忆。在味蕾的窖藏中,渣肉是有一席之地的,粘粉是中秋节回去带回的——每次回家,母亲总会让我带点孩提时爱吃的东西,我深知那是母亲予我的挂牵和家的味道。以前,做渣肉的粘粉是用柴火锅巴研磨成碎取用的,风干几日的渣肉用干荷叶托底上笼屉蒸熟,厨房的氤氲气都透着馋人的香味,一块渣肉入口糯而不腻,香软生津,米饭总得多吃上一碗。现在,大锅柴火锅巴难寻见了,快餐化的食材方便了赶路和蜗居的人,没了日头的烟熏火燎,很多味道寡淡了许多。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有阳光的冬日,在街头慢慢走一走,去市井无目的地转一转,时常会有想不到的物件解锁你麻木的神经,触碰你内心的柔软之处,打开你的记忆密码,感动到你,这种感觉真是很久违、很滋养。
有点遗憾,今年终究是错过了一些时景,山科大的银杏、大珠山的红枫、鱼鸣嘴的渔歌唱晚、唐岛湾湿地公园的落霞与孤鹜,毛家山的清泉……还有很多以前常去的地方,稀疏了亲近。记得疫情起始时,我坚持每天步行上下班,沿途的市井烟火无形中关注多了,心情放松了,身体强健了,还收获了不少慰藉,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入冬后,沿街叫卖白菜和萝卜的多了起来,偶尔还有古法爆米花的,手艺人摇柄吱嘎声中,泥炉里忽大忽小蹿起的火苗透着暖意,稍不留神,出锅起爆的声响冷不丁会吓你一跳。欣喜地看到几家晾晒干鱼的杂货铺,有的将鱼铺在网上,有的把鱼悬挂在绳上,鲅鱼我是认得的,别的就叫不出名了,但都充满浓郁的海洋气息,让人不由得驻足发呆片刻。
这个季节,想必在家乡,也到了制作挂面、腌制咸菜和腊味的时候了。江南村户人家习惯伴水而居,即便通了自来水,也改变不了一些妇人在池塘里洗刷的习惯,每个池塘一般都会有一块青石板在缓坡处伸到水中,那是浣衣淘洗时的蹲脚处,也是夏天孩子们戏水的跳板,棒槌有节奏的敲拍声,妇人相互间家长里短的唏嘘声,无不透着日子的鲜活。
进了腊月门,家家户户在晴好天都会在池前空地上支起架绳,或是在屋檐下钉上挂钩,把腌制品挂在阳光下晾晒、风干。有炊烟升起,有鸡鸣犬吠,有芦花摇曳。日头西落,总有大人一边将晾晒的咸鱼、腊肉等往家里收,一边大声吆喝孩子回家吃饭,拖长的音调在石板巷久久回响,这样的记忆片段某一刻会不自觉在脑海中丝丝泛起,清晰又模糊,美好着、温暖着,迟滞你匆行的脚步。
冬日的暖阳,可以催生出很多美味记忆。在味蕾的窖藏中,渣肉是有一席之地的,粘粉是中秋节回去带回的——每次回家,母亲总会让我带点孩提时爱吃的东西,我深知那是母亲予我的挂牵和家的味道。以前,做渣肉的粘粉是用柴火锅巴研磨成碎取用的,风干几日的渣肉用干荷叶托底上笼屉蒸熟,厨房的氤氲气都透着馋人的香味,一块渣肉入口糯而不腻,香软生津,米饭总得多吃上一碗。现在,大锅柴火锅巴难寻见了,快餐化的食材方便了赶路和蜗居的人,没了日头的烟熏火燎,很多味道寡淡了许多。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有阳光的冬日,在街头慢慢走一走,去市井无目的地转一转,时常会有想不到的物件解锁你麻木的神经,触碰你内心的柔软之处,打开你的记忆密码,感动到你,这种感觉真是很久违、很滋养。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