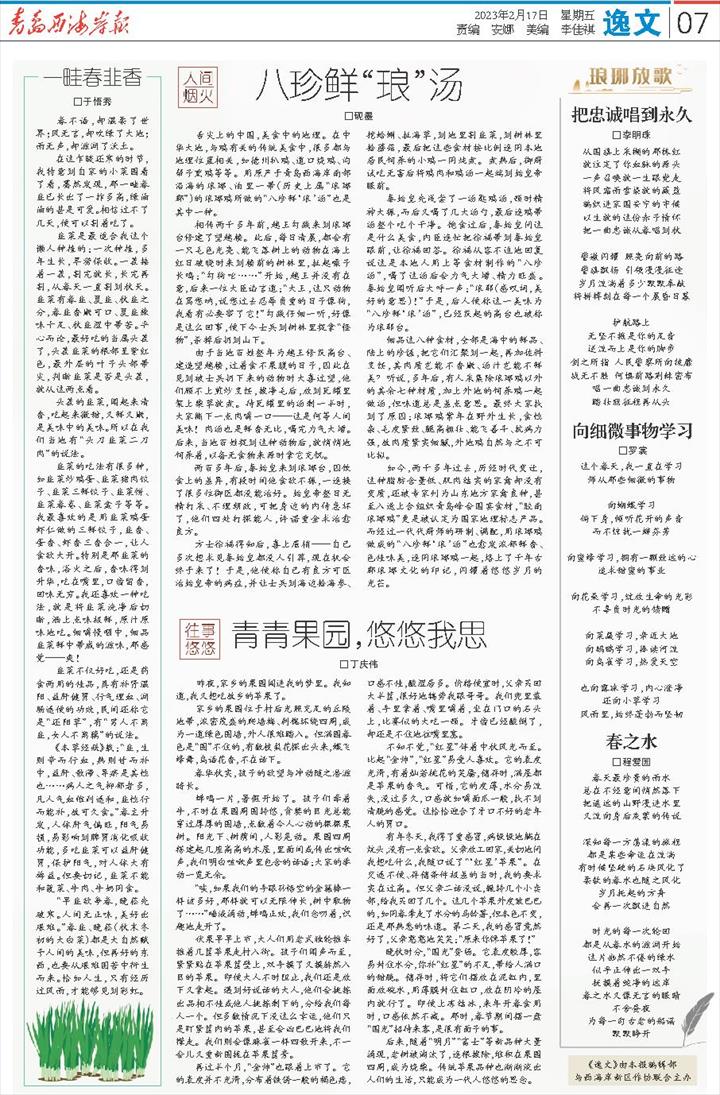文章内容
青青果园,悠悠我思
□丁庆伟
昨夜,家乡的果园闯进我的梦里。我知道,我又想吃故乡的苹果了。
家乡的果园位于村后光照充足的丘陵地带,浓密茂盛的爬墙梅、刺槐环绕四周,成为一道绿色围墙,外人很难踏入。但满园春色是“围”不住的,有数枝梨花探出头来,蝶飞蜂舞,鸟语花香,不在话下。
春华秋实,孩子的欲望与冲动随之潜滋暗长。
蝉鸣一片,暑假开始了。孩子们牵着牛,不时在果园周围转悠,贪婪的目光总能穿过厚厚的围墙,点数着令人心动的棵棵果树。阳光下、树荫间,人影晃动。果园四周搭建起几座高高的木屋,里面间或传出咳嗽声,我们明白咳嗽声里包含的话语:大家的举动一览无余。
“唉,如果我们的手跟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该多好,那样就可以无限伸长,树中取物了……”唾液涌动,蝉鸣正欢,我们念叨着,识趣地走开了。
伏果早早上市,大人们用老式独轮推车推着几筐苹果走村入街。孩子们闻声而至,紧紧贴在苹果筐壁上,双手摸了又摸赫然入目的苹果。即便大人不时阻止,我们还是放下又拿起。遇到好说话的大人,他们会挑拣出品相不佳或他人挑拣剩下的,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但多数情况下没这么幸运,他们只是盯紧筐内的苹果,甚至会凶巴巴地将我们撵走。我们则会像麻雀一样四散开来,不一会儿又重新围拢在苹果筐旁。
再过半个月,“金帅”也跟着上市了。它的表皮并不光滑,分布着铁锈一般的褐色痣,口感不佳,酸涩居多。价格便宜时,父亲买回大半筐,很好地犒劳我跟哥哥。我们兜里装着、手里拿着、嘴里嚼着,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比赛似的大吃一顿。牙齿已经酸倒了,却还是不住地往嘴里塞。
不知不觉,“红星”伴着中秋风光而至。比起“金帅”,“红星”易受人喜欢。它的表皮光滑,有着灿若桃花的笑靥,储存时,满屋都是苹果的香气。可惜,它的皮薄,水分易流失,没过多久,口感就如嚼面瓜一般,找不到清脆的感觉。这恰恰迎合了牙口不好的老年人的胃口。
有年冬天,我得了重感冒,病恹恹地躺在炕头,没有一点食欲。父亲放工回家,关切地问我想吃什么,我随口说了“‘红星’苹果”。在交通不便、存储条件极差的当时,我的要求实在过高。但父亲二话没说,辗转几个小卖部,给我买回了几个。这几个苹果外皮皱巴巴的,如同春季走了水分的马铃薯,但本色不变,还是那熟悉的味道。第二天,我的感冒竟然好了,父亲憨憨地笑笑:“原来你馋苹果了!”
晚秋时分,“国光”登场。它表皮较厚,容易封住水分,弥补“红星”的不足,带给人满口的甜脆。储存时,将它们摆放在泥缸内,里面放碗水,用薄膜封住缸口,放在阴冷的屋内就行了。即便上冻结冰,来年开春食用时,口感依然不减。那时,春节期间摆一盘“国光”招待来客,是很有面子的事。
后来,随着“明月”“富士”等新品种大量涌现,老树被淘汰了,连根拔除,堆积在果园四周,成为烧柴。传统苹果品种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只能成为一代人悠悠的思念。
昨夜,家乡的果园闯进我的梦里。我知道,我又想吃故乡的苹果了。
家乡的果园位于村后光照充足的丘陵地带,浓密茂盛的爬墙梅、刺槐环绕四周,成为一道绿色围墙,外人很难踏入。但满园春色是“围”不住的,有数枝梨花探出头来,蝶飞蜂舞,鸟语花香,不在话下。
春华秋实,孩子的欲望与冲动随之潜滋暗长。
蝉鸣一片,暑假开始了。孩子们牵着牛,不时在果园周围转悠,贪婪的目光总能穿过厚厚的围墙,点数着令人心动的棵棵果树。阳光下、树荫间,人影晃动。果园四周搭建起几座高高的木屋,里面间或传出咳嗽声,我们明白咳嗽声里包含的话语:大家的举动一览无余。
“唉,如果我们的手跟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该多好,那样就可以无限伸长,树中取物了……”唾液涌动,蝉鸣正欢,我们念叨着,识趣地走开了。
伏果早早上市,大人们用老式独轮推车推着几筐苹果走村入街。孩子们闻声而至,紧紧贴在苹果筐壁上,双手摸了又摸赫然入目的苹果。即便大人不时阻止,我们还是放下又拿起。遇到好说话的大人,他们会挑拣出品相不佳或他人挑拣剩下的,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但多数情况下没这么幸运,他们只是盯紧筐内的苹果,甚至会凶巴巴地将我们撵走。我们则会像麻雀一样四散开来,不一会儿又重新围拢在苹果筐旁。
再过半个月,“金帅”也跟着上市了。它的表皮并不光滑,分布着铁锈一般的褐色痣,口感不佳,酸涩居多。价格便宜时,父亲买回大半筐,很好地犒劳我跟哥哥。我们兜里装着、手里拿着、嘴里嚼着,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比赛似的大吃一顿。牙齿已经酸倒了,却还是不住地往嘴里塞。
不知不觉,“红星”伴着中秋风光而至。比起“金帅”,“红星”易受人喜欢。它的表皮光滑,有着灿若桃花的笑靥,储存时,满屋都是苹果的香气。可惜,它的皮薄,水分易流失,没过多久,口感就如嚼面瓜一般,找不到清脆的感觉。这恰恰迎合了牙口不好的老年人的胃口。
有年冬天,我得了重感冒,病恹恹地躺在炕头,没有一点食欲。父亲放工回家,关切地问我想吃什么,我随口说了“‘红星’苹果”。在交通不便、存储条件极差的当时,我的要求实在过高。但父亲二话没说,辗转几个小卖部,给我买回了几个。这几个苹果外皮皱巴巴的,如同春季走了水分的马铃薯,但本色不变,还是那熟悉的味道。第二天,我的感冒竟然好了,父亲憨憨地笑笑:“原来你馋苹果了!”
晚秋时分,“国光”登场。它表皮较厚,容易封住水分,弥补“红星”的不足,带给人满口的甜脆。储存时,将它们摆放在泥缸内,里面放碗水,用薄膜封住缸口,放在阴冷的屋内就行了。即便上冻结冰,来年开春食用时,口感依然不减。那时,春节期间摆一盘“国光”招待来客,是很有面子的事。
后来,随着“明月”“富士”等新品种大量涌现,老树被淘汰了,连根拔除,堆积在果园四周,成为烧柴。传统苹果品种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只能成为一代人悠悠的思念。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