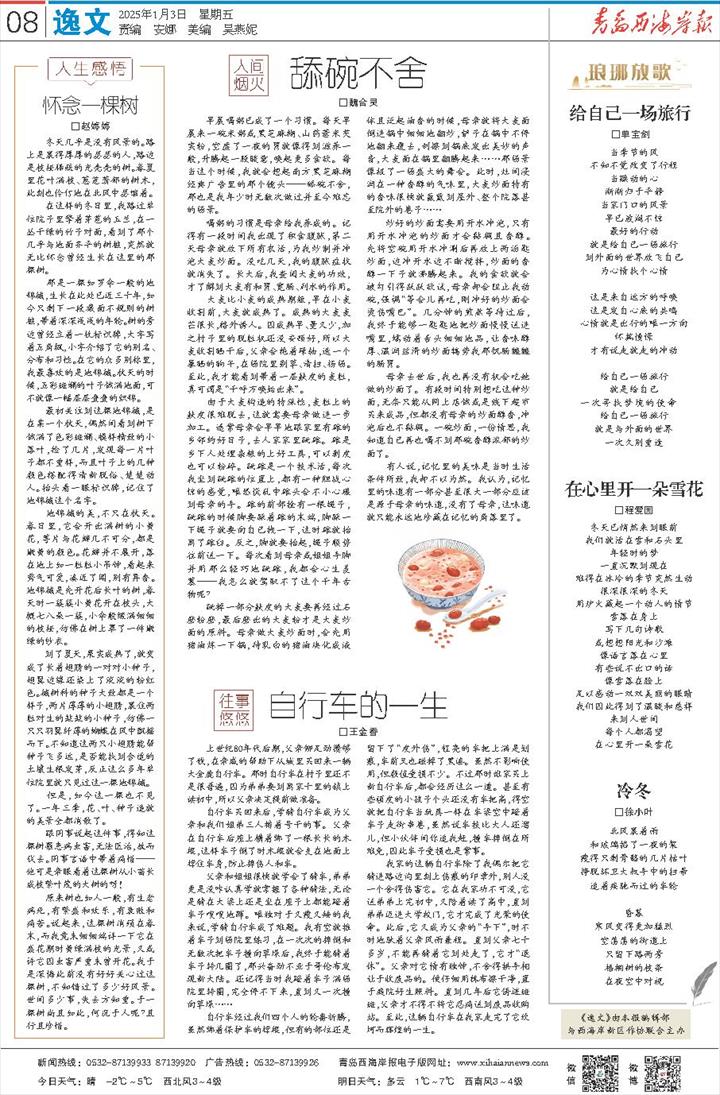文章内容
舔碗不舍
□魏合灵
早晨喝粥已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来一碗米粥或黑芝麻糊、山药薏米芡实粉,空虚了一夜的胃就像得到滋养一般,升腾起一股暖意,唤起更多食欲。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南方黑芝麻糊经典广告里的那个镜头——舔碗不舍,那也是我年少时无数次做过并至今难忘的场景。
喝粥的习惯是母亲给我养成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出现了积食腹胀,第二天母亲就放下所有农活,为我炒制并冲泡大麦炒面。没吃几天,我的腹胀症状就消失了。长大后,我查阅大麦的功效,才了解到大麦有和胃、宽肠、利水的作用。
大麦比小麦的成熟期短,早在小麦收割前,大麦就成熟了。成熟的大麦麦芒很长,格外诱人。因成熟早、量又少,加之村子里的脱粒机还没安顿好,所以大麦收割晒干后,父亲会拖着碌轴,选一个暴晒的晌午,在场院里剔草、清扫、扬场。至此,我才能看到带着一层麸皮的麦粒,真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由于大麦构造的特殊性,麦粒上的麸皮很难脱去,这就需要母亲做进一步加工。通常母亲会早早地跟家里有碓的乡邻约好日子,去人家家里跐碓。碓是乡下人处理杂粮的上好工具,可以剥皮也可以粉碎。跐碓是一个技术活,每次我坐到跐碓的位置上,都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唯恐慌乱中碓头会不小心碾到母亲的手。碓的前部拴有一根绳子,跐碓的时候脚要踩着碓的末端,脚踩一下绳子就要向自己拽一下,这时碓就抬离了碓臼。反之,脚就要抬起,绳子顺势往前送一下。每次看到母亲或姐姐手脚并用那么轻巧地跐碓,我都会心生羡慕——我怎么就驾驭不了这个千年古物呢?
跐掉一部分麸皮的大麦要再经过石磨粉磨,最后磨出的大麦粉才是大麦炒面的原料。母亲做大麦炒面时,会先用猪油炼一下锅,待乳白的猪油块化成液体且泛起油香的时候,母亲就将大麦面倒进锅中细细地翻炒,铲子在锅中不停地翻来覆去,刮擦到锅底发出美妙的声音,大麦面在锅里翻腾起来……那场景像极了一场盛大的舞会。此时,灶间浸润在一种香醇的气味里,大麦炒面特有的香味很快就氤氲到屋外、整个院落甚至院外的巷子……
炒好的炒面需要用开水冲泡,只有用开水冲泡的炒面才会黏稠且香醇。先将空碗用开水冲涮后再放上两汤匙炒面,边冲开水边不断搅拌,炒面的香醇一下子就沸腾起来。我的食欲就会被勾引得跃跃欲试,母亲却会阻止我动碗,强调“等会儿再吃,刚冲好的炒面会烫伤嘴巴”。几分钟的煎熬等待过后,我终于能够一匙匙地把炒面慢慢送进嘴里,蠕动着舌头细细地品,让香味醇厚、温润丝滑的炒面犒劳我那饥肠辘辘的肠胃。
母亲去世后,我也再没有机会吃她做的炒面了。有段时间特别想吃这种炒面,无奈只能从网上店铺或是线下超市买来成品,但都没有母亲的炒面醇香,冲泡后也不黏稠。一碗炒面,一份情思,我知道自己再也喝不到那碗香醇浓郁的炒面了。
有人说,记忆里的美味是当时生活条件所致,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记忆里的味道有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源于母亲的味道,没有了母亲,这味道就只能永远地珍藏在记忆的角落里了。
早晨喝粥已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来一碗米粥或黑芝麻糊、山药薏米芡实粉,空虚了一夜的胃就像得到滋养一般,升腾起一股暖意,唤起更多食欲。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南方黑芝麻糊经典广告里的那个镜头——舔碗不舍,那也是我年少时无数次做过并至今难忘的场景。
喝粥的习惯是母亲给我养成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出现了积食腹胀,第二天母亲就放下所有农活,为我炒制并冲泡大麦炒面。没吃几天,我的腹胀症状就消失了。长大后,我查阅大麦的功效,才了解到大麦有和胃、宽肠、利水的作用。
大麦比小麦的成熟期短,早在小麦收割前,大麦就成熟了。成熟的大麦麦芒很长,格外诱人。因成熟早、量又少,加之村子里的脱粒机还没安顿好,所以大麦收割晒干后,父亲会拖着碌轴,选一个暴晒的晌午,在场院里剔草、清扫、扬场。至此,我才能看到带着一层麸皮的麦粒,真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由于大麦构造的特殊性,麦粒上的麸皮很难脱去,这就需要母亲做进一步加工。通常母亲会早早地跟家里有碓的乡邻约好日子,去人家家里跐碓。碓是乡下人处理杂粮的上好工具,可以剥皮也可以粉碎。跐碓是一个技术活,每次我坐到跐碓的位置上,都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唯恐慌乱中碓头会不小心碾到母亲的手。碓的前部拴有一根绳子,跐碓的时候脚要踩着碓的末端,脚踩一下绳子就要向自己拽一下,这时碓就抬离了碓臼。反之,脚就要抬起,绳子顺势往前送一下。每次看到母亲或姐姐手脚并用那么轻巧地跐碓,我都会心生羡慕——我怎么就驾驭不了这个千年古物呢?
跐掉一部分麸皮的大麦要再经过石磨粉磨,最后磨出的大麦粉才是大麦炒面的原料。母亲做大麦炒面时,会先用猪油炼一下锅,待乳白的猪油块化成液体且泛起油香的时候,母亲就将大麦面倒进锅中细细地翻炒,铲子在锅中不停地翻来覆去,刮擦到锅底发出美妙的声音,大麦面在锅里翻腾起来……那场景像极了一场盛大的舞会。此时,灶间浸润在一种香醇的气味里,大麦炒面特有的香味很快就氤氲到屋外、整个院落甚至院外的巷子……
炒好的炒面需要用开水冲泡,只有用开水冲泡的炒面才会黏稠且香醇。先将空碗用开水冲涮后再放上两汤匙炒面,边冲开水边不断搅拌,炒面的香醇一下子就沸腾起来。我的食欲就会被勾引得跃跃欲试,母亲却会阻止我动碗,强调“等会儿再吃,刚冲好的炒面会烫伤嘴巴”。几分钟的煎熬等待过后,我终于能够一匙匙地把炒面慢慢送进嘴里,蠕动着舌头细细地品,让香味醇厚、温润丝滑的炒面犒劳我那饥肠辘辘的肠胃。
母亲去世后,我也再没有机会吃她做的炒面了。有段时间特别想吃这种炒面,无奈只能从网上店铺或是线下超市买来成品,但都没有母亲的炒面醇香,冲泡后也不黏稠。一碗炒面,一份情思,我知道自己再也喝不到那碗香醇浓郁的炒面了。
有人说,记忆里的美味是当时生活条件所致,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记忆里的味道有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源于母亲的味道,没有了母亲,这味道就只能永远地珍藏在记忆的角落里了。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