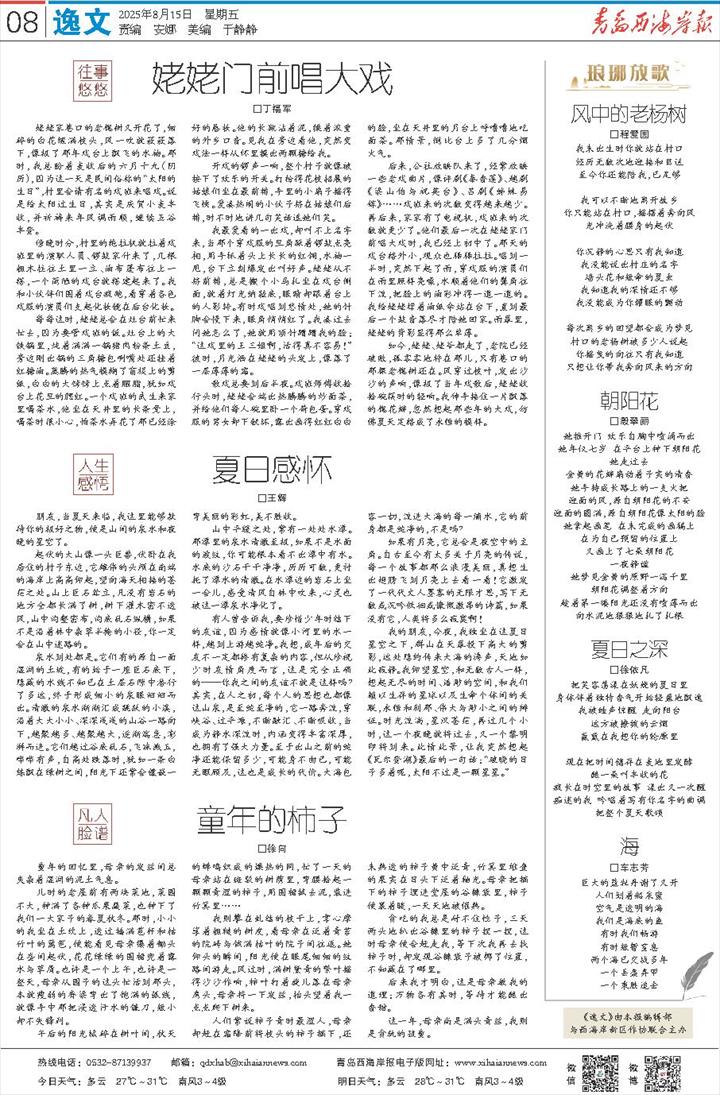文章内容
姥姥门前唱大戏
□丁福军
姥姥家巷口的老槐树又开花了,细碎的白花缀满枝头,风一吹就簌簌落下,像极了那年戏台上飘飞的水袖。那时,我总盼着麦收后的六月十九(阴历),因为这一天是民间俗称的“太阳的生日”,村里会请有名的戏班来唱戏。说是给太阳过生日,其实是庆贺小麦丰收,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继续五谷丰登。
傍晚时分,村里的拖拉机就拉着戏班里的演职人员、锣鼓家什来了,几根粗木柱往土里一立、油布篷布往上一搭,一个简陋的戏台就搭建起来了。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戏台疯跑,看穿着各色戏服的演员们支起化妆镜在后台化妆。
每每这时,姥姥总会在灶台前忙来忙去,因为要管戏班的饭。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炖着满满一锅猪肉粉条土豆,旁边刚出锅的三角糖包咧嘴处还挂着红糖油。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棂上的剪纸,白白的大饽饽上点着胭脂,犹如戏台上花旦的腮红。一个戏班的武生来家里喝茶水,他坐在天井里的长条凳上,喝茶时很小心,怕茶水弄花了那已经涂好的唇妆。他的长靴沾着泥,操着浓重的外乡口音。见我在旁边看他,突然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摸出两颗糖给我。
开戏的锣声一响,整个村子就像被按下了欢乐的开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坐在最前排,手里的小扇子摇得飞快。爱凑热闹的小伙子挤在姑娘们后排,时不时地讲几句笑话逗她们笑。
我最爱看的一出戏,却叫不上名字来,当那个穿戏服的旦角踩着锣鼓点亮相,用手抓着头上长长的红翎,水袖一甩,台下立刻爆发出叫好声。姥姥从不挤前排,总是搬个小马扎坐在戏台侧面,就着灯光纳鞋底,眼睛却跟着台上的人影转。有时戏唱到悲情处,她的针脚会慢下来,眼角悄悄红了。我凑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就用顶针蹭蹭我的脸:“这戏里的王三姐啊,活得真不容易!”彼时,月光洒在姥姥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
散戏总要到后半夜。戏班师傅收拾行头时,姥姥会端出热腾腾的炒面茶,并给他们每人碗里卧一个荷包蛋。穿戏服的男女卸下钗环,露出画得红红白白的脸,坐在天井里的月台上呼噜噜地吃面茶。那情景,倒比台上多了几分烟火气。
后来,公社放映队来了,经常放映一些老戏曲片,像评剧《秦香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吕剧《姊妹易嫁》……戏班来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再后来,家家有了电视机,戏班来的次数就更少了。他们最后一次在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时,我已经上初中了。那天的戏台格外小,观众也稀稀拉拉。唱到一半时,突然下起了雨,穿戏服的演员们在雨里照样亮嗓,水顺着他们的鬓角往下流,把脸上的油彩冲得一道一道的。我给姥姥撑着油纸伞站在台下,直到最后一个鼓音落尽才陪她回家。雨幕里,姥姥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
如今,姥姥、姥爷都走了,老院已经破败,孤零零地杵在那儿,只有巷口的那棵老槐树还在。风穿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当年戏散后,姥姥收拾碗筷时的轻响。我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槐花瓣,忽然想起那些年的大戏,仿佛夏天定格成了永恒的模样。
姥姥家巷口的老槐树又开花了,细碎的白花缀满枝头,风一吹就簌簌落下,像极了那年戏台上飘飞的水袖。那时,我总盼着麦收后的六月十九(阴历),因为这一天是民间俗称的“太阳的生日”,村里会请有名的戏班来唱戏。说是给太阳过生日,其实是庆贺小麦丰收,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继续五谷丰登。
傍晚时分,村里的拖拉机就拉着戏班里的演职人员、锣鼓家什来了,几根粗木柱往土里一立、油布篷布往上一搭,一个简陋的戏台就搭建起来了。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戏台疯跑,看穿着各色戏服的演员们支起化妆镜在后台化妆。
每每这时,姥姥总会在灶台前忙来忙去,因为要管戏班的饭。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炖着满满一锅猪肉粉条土豆,旁边刚出锅的三角糖包咧嘴处还挂着红糖油。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棂上的剪纸,白白的大饽饽上点着胭脂,犹如戏台上花旦的腮红。一个戏班的武生来家里喝茶水,他坐在天井里的长条凳上,喝茶时很小心,怕茶水弄花了那已经涂好的唇妆。他的长靴沾着泥,操着浓重的外乡口音。见我在旁边看他,突然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摸出两颗糖给我。
开戏的锣声一响,整个村子就像被按下了欢乐的开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坐在最前排,手里的小扇子摇得飞快。爱凑热闹的小伙子挤在姑娘们后排,时不时地讲几句笑话逗她们笑。
我最爱看的一出戏,却叫不上名字来,当那个穿戏服的旦角踩着锣鼓点亮相,用手抓着头上长长的红翎,水袖一甩,台下立刻爆发出叫好声。姥姥从不挤前排,总是搬个小马扎坐在戏台侧面,就着灯光纳鞋底,眼睛却跟着台上的人影转。有时戏唱到悲情处,她的针脚会慢下来,眼角悄悄红了。我凑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就用顶针蹭蹭我的脸:“这戏里的王三姐啊,活得真不容易!”彼时,月光洒在姥姥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
散戏总要到后半夜。戏班师傅收拾行头时,姥姥会端出热腾腾的炒面茶,并给他们每人碗里卧一个荷包蛋。穿戏服的男女卸下钗环,露出画得红红白白的脸,坐在天井里的月台上呼噜噜地吃面茶。那情景,倒比台上多了几分烟火气。
后来,公社放映队来了,经常放映一些老戏曲片,像评剧《秦香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吕剧《姊妹易嫁》……戏班来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再后来,家家有了电视机,戏班来的次数就更少了。他们最后一次在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时,我已经上初中了。那天的戏台格外小,观众也稀稀拉拉。唱到一半时,突然下起了雨,穿戏服的演员们在雨里照样亮嗓,水顺着他们的鬓角往下流,把脸上的油彩冲得一道一道的。我给姥姥撑着油纸伞站在台下,直到最后一个鼓音落尽才陪她回家。雨幕里,姥姥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
如今,姥姥、姥爷都走了,老院已经破败,孤零零地杵在那儿,只有巷口的那棵老槐树还在。风穿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当年戏散后,姥姥收拾碗筷时的轻响。我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槐花瓣,忽然想起那些年的大戏,仿佛夏天定格成了永恒的模样。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