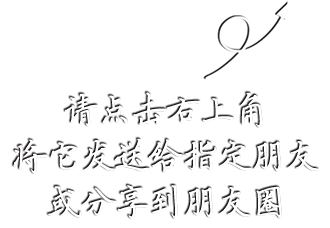贴春联
青岛西海岸报
2024年02月19日
□刘培蕊
小时候,我经常帮父亲贴春联。除夕早上吃过早饭,母亲就会用白面熬一小盆面糊当浆糊备用。她熬浆糊的手艺很高,不厚不薄、恰到好处,冒着热气的浆糊那么白那么香,我总会忍不住找来匙子尝几口。每每这时,母亲总会笑眯眯地瞅我一眼,递给我一个刷子说:“别烫着,喝完了帮你大大贴春联去!”我顾不上答应,只连连点头。
贴春联是个技术活,小的春联好说,把春联反铺在桌子上,用刷子蘸着浆糊,均匀地涂一遍,尤其注意四个边角。涂得太厚浆糊就可能洇到正面,正面的红色就会掉色;涂得薄了可能粘不住,没几天,风一刮就掉下来了,不吉利。
除了涂浆糊,小的春联以及“福”字,基本我都抢着去贴,也因此慢慢了解了很多贴春联的“学问”。比如,“人口平安”贴在炕头一面的门后墙上,“年年有余”贴在堂屋门正上方,“六畜兴旺”贴在鸡鸭圈的门栏上,“大耳元帅”贴在猪圈的栅门边,还有一个“出门见喜”要贴在大门口对面的墙上。而家里盛满粮食的缸、石磨、小推车等大件,甚至院子里的水井、枣树等,都可以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
最有趣的当然是贴在大门口的春联。由于父亲不认识字,所以每次都会问我:“丫头,这张贴哪边?”刚认识几个字的我,自然不知道上下联之分,所以每次都把父亲手里的春联,认真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让我头痛的是,这些对联怎么读都顺口。比如“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年年顺景财源广,岁岁平安福寿多”“和风沐浴三春暖,厚德包容一脉香”等等。没办法,我假装思考一番,用手一指,坚定地说:“这个左边,这个右边。”父亲深信不疑,很认真地贴上了。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上了高中,才知道春联竟是很有些讲究的。仅以使用的场所而论,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批、春条、斗斤等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批”贴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具、影壁中。此时,再回头想想自己告诉父亲的上下联,竟然大多都是倒的,不禁汗颜。
多年之后,上三年级的儿子为完成寒假作业,大年初一冒着小雪串门拜年,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仔细地把每一家门上的春联抄录下来。而我也耐心地给儿子一一讲解,慢慢陪着他抄录,让他从小就能体会春联的魅力。看着儿子冻得通红的小脸上开心的笑容,才让我对少时的错误得以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