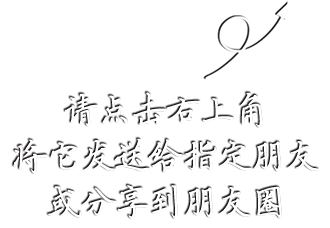辣椒给予的幸福
青岛西海岸报
2025年03月14日
□崔启昌
俗语言:四川人不怕辣,江西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胶州湾畔的青岛人对于辣味是啥感觉?这事搁早些年说来有些不好意思启齿。举个例子:青岛人去酒楼食肆吃火锅,往往人影未见声先到,大呼小叫地嚷着微辣、微辣。等到人家店员按微辣要求点碳生火至锅沸菜熟时,试探着执箸夹菜,八成是刚碰到舌尖儿吧,青岛人就会有些夸张地龇牙咧嘴、面面相觑,继而大汗淋漓,或者眼泪汪汪。微辣竟能如此,要是如川黔湘赣的食客那样直面真正的辣滋味,青岛人肯定会愧对满桌佳肴,说不定早就唯恐避之不及地逃之夭夭了。
辣椒在烹饪界地位很高,用它做调料据说可去腥膻、解油腻。从饮食角度讲,由于辣椒素的作用,辣椒能刺激唾液分泌,使人增进食欲。此外,辣椒还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让人兴奋,提振精神。从医学角度看,辣椒具有温中下气、开胃消食、散寒除湿的作用。据说常食辣椒的人,很少得风湿性关节炎和冻疮。照理说,青岛人大多住在海边,而海边湿气重,多吃些辣椒有益无害。可是,甭管把辣椒说得怎么天花乱坠,青岛人就是无动于衷——爱咋的咋的,任你食材地位高到天上去,就是不稀罕!
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的辣椒,在种植面积上越来越呈燎原之势。想这“俨似秃笔头”的小小辣子一乘声名远扬的丝绸之路,从西亚经中亚进入新疆、甘肃、陕西等地,率先在西北落地生根;二经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在云南、广西和湖南等地开花结果,然后逐渐向全国扩展,到现在,偌大的中国几乎没有辣椒的空白地带了。
作为一个不擅吃辣的青岛人,我领教过若干嗜辣者的真功夫。湖南人将白花花的大米饭用辣椒酱染成吓人的紫红色,风卷残云,汗流浃背,一通狼吞虎咽,米干碗净。四川人把一铝盆泛着油花亮光、溢着辣香气味的鱼头汤仰脖咽下,抹了额头上的汗珠子,竟还高呼:“再来一盆,别忘多搁些辣椒和花椒!”江西人临近午饭时,常从衣袋里掏出掖藏的干辣椒咀嚼着安抚饥饿了的肠胃,细嚼慢咽,津津有味。
近几年,因私旅或公差,我到过南方多座城市。每到饭点,总有一事犯难:愁着吃含辣的东西。而以不敢吃辣为由,央求店家捣弄几碟小炒上桌时,得到的多半是“离了辣椒,厨师炒不得菜哩”的答复。无奈,经常是随口要碗蛋炒饭,再附上几方齁咸的臭豆腐,拌一盘姜汁皮蛋,急急扒拉着吃了拉倒。
有一年正月,和朋友结伴去江西婺源看油菜花。彼时,青岛还是白雪覆地,而婺源已然燕舞莺歌、花香馥郁了。登高望远,满眼鲜艳,真真滋润了好心情。愁就愁在伙食上,沿婺源县城大街小巷几乎寻了个遍,酒楼食肆炒菜一律含辣。“微辣,行吗?”商量的口吻,换来的只是微笑和摇头。三天,除了泡面、榨菜,最幸福的一顿是与朋友一起说服街边的一农家宴,让我们亲自下厨,急火爆炒了青苔菜。炒菜时只把葱姜蒜当调料,一丝辣椒没搁,鲜香在厨房缭绕撒散,食欲愈发肆意,每人两碗米饭一盘菜,吃得那叫一个熨帖!
说青岛人不吃辣现在看来不准确了,这也倒是顺应了一种借鉴、演变、传承和发展的规律。如今的社会进步快,舌尖上的美味以及由美味带来的幸福,往往来得很自然。比如青岛人爱吃辣炒蛤蜊,那真是一绝。蛤蜊本来极鲜,清蒸或水煮便是上好菜肴。油热,加葱花、青红辣椒爆炒,至蛤蜊开口时再加香菜末,出锅装盘。你尝尝,这味道鲜中泛着淡淡的辣滋味,谁都享用得了,且谁都说好。“这是辣椒给予的幸福。”有位市民接受采访时说的这句话,道出了青岛人的心声。
如今,青岛人已不再谈辣色变,不再遇辣拒吃,这都得感谢社会的发展。这些年,每遇饭点,青岛的街巷间会有渐浓的辣椒香弥散,溜达着瞅瞅,什么辣子鸡、剁椒鱼头、麻辣香锅之类以“辣”为主调的菜品举不胜举,饕餮一碗美滋味的也不光是年轻人,耄耋老人落座入席当食客的大有人在。
学者符中士先生在《吃的自由》一书中说:“长期大量吃辣椒,人自然要勇敢刚烈。勇敢刚烈的程度,似乎与吃辣的辣度成正比。”他拿湖南人作比较,说嗜辣如命的湘中山民,比辣得温和的湘北湖区农民火气就足得多。符先生认为,这种辣椒培养出来的民风,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瞧瞧,吃辣椒还有这样的功效呢。
我觉得,吃惯了生猛海鲜的青岛人,随着社会进步的节拍,不妨渐进地跟辣椒周旋一番,斗一斗,让血脉更加通畅,让意气愈加飞扬。时间一长,成了习惯,说不定会体会到辣椒给予的更多幸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