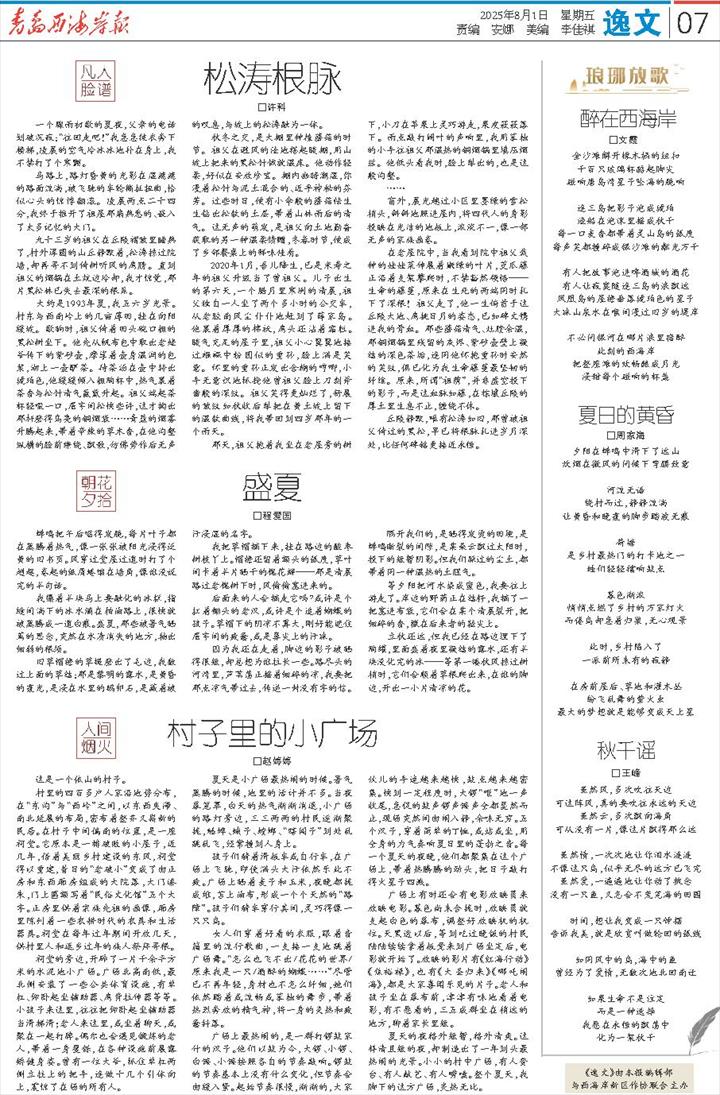文章内容
松涛根脉
□许科
一个骤雨初歇的夏夜,父亲的电话划破沉寂:“往回走吧!”我急急披衣奔下楼梯,凌晨的空气冷冰冰地扑在身上,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马路上,路灯昏黄的光影在湿漉漉的路面流淌,被飞驰的车轮撕扯扭曲,恰似心头的惊悸翻滚。凌晨两点二十四分,我终于推开了祖屋那扇熟悉的、嵌入了太多记忆的大门。
九十三岁的祖父在丘陵褶皱里睡熟了,村外浑圆的山丘静默着,松涛掠过院墙,却再寻不到倚树听风的肩膀。直到祖父的烟锅在土炕边冷却,我才惊觉,那片黑松林已失去最深的根系。
大约是1993年夏,我五六岁光景。村东与西南岭上的几亩薄田,挂在向阳缓坡。歇晌时,祖父倚着田头碗口粗的黑松树坐下。他先从帆布包中取出老姥爷传下的紫砂壶,摩挲着壶身温润的包浆,沏上一壶酽茶。待茶汤在壶中转出琥珀色,他缓缓倾入粗陶杯中,热气裹着茶香与松针清气氤氲升起。祖父端起茶杯轻啜一口,眉宇间松快些许,这才掏出那杆磨得乌亮的铜烟袋……青蓝的烟雾升腾起来,带着辛辣的草木香,在他沟壑纵横的脸前缭绕、飘散,仿佛劳作后无声的叹息,与坡上的松涛融为一体。
秋冬之交,是大棚里种植蘑菇的时节。祖父在避风的洼地搭起暖棚,用山坡上耙来的黑松针铺就温床。他动作轻柔,好似在安放珍宝。棚内幽暗潮湿,弥漫着松针与泥土混合的、近乎神秘的芬芳。过些时日,便有小伞般的蘑菇怯生生钻出松软的土层,带着山林雨后的清气。这无声的萌发,是祖父向土地勤奋获取的另一种温柔馈赠,冬春时节,便成了乡邻餐桌上的鲜味佳肴。
2020年1月,吾儿降生,已是米寿之年的祖父升级当了曾祖父。儿子出生的第六天,一个腊月里寒冽的清晨,祖父独自一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老胶南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薛家岛。他裹着厚厚的棉袄,肩头还沾着霜粒。暖气充足的屋子里,祖父小心翼翼地接过襁褓中粉团似的重孙,脸上满是笑意。怀里的重孙正发出含糊的哼唧,小手无意识地抓挠他曾祖父脸上刀刻斧凿般的深纹。祖父笑得更灿烂了,舒展的皱纹如秋收后犁耙在黄土坡上留下的温软曲线,将我带回到四岁那年的一个雨天。
那天,祖父抱着我坐在老屋旁的树下,小刀在苹果上灵巧游走,果皮簌簌落下。雨点敲打阔叶的声响里,我用笨拙的小手往祖父那温热的铜烟锅里填压烟丝。他低头看我时,脸上犁出的,也是这般沟壑。
……
窗外,晨光越过小区里墨绿的雪松梢头,斜斜地照进屋内,将四代人的身影投映在光洁的地板上,浓淡不一,像一部无声的家族画卷。
在老屋院中,当我看到院中祖父栽种的娃娃菜伸展着嫩绿的叶片,茭瓜藤正沿着支架攀爬时,不禁豁然领悟——生命的藤蔓,原来在生死的两端同时扎下了深根!祖父走了,他一生俯首于这丘陵大地、肩挑日月的姿态,已如碑文镌进我的骨血。那些蘑菇清气、灶膛余温,那铜烟锅里残留的灰烬、紫砂壶壁上凝结的深色茶垢,连同他怀抱重孙时安然的笑纹,俱已化为我生命藤蔓最坚韧的纤维。原来,所谓“祖荫”,并非虚空投下的影子,而是这血脉如藤,在棕壤丘陵的厚土里生息不止,缠绕不休。
丘陵静默,唯有松涛如旧,那曾被祖父倚过的黑松,早已将根脉扎进岁月深处,比任何碑铭更接近永恒。
一个骤雨初歇的夏夜,父亲的电话划破沉寂:“往回走吧!”我急急披衣奔下楼梯,凌晨的空气冷冰冰地扑在身上,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马路上,路灯昏黄的光影在湿漉漉的路面流淌,被飞驰的车轮撕扯扭曲,恰似心头的惊悸翻滚。凌晨两点二十四分,我终于推开了祖屋那扇熟悉的、嵌入了太多记忆的大门。
九十三岁的祖父在丘陵褶皱里睡熟了,村外浑圆的山丘静默着,松涛掠过院墙,却再寻不到倚树听风的肩膀。直到祖父的烟锅在土炕边冷却,我才惊觉,那片黑松林已失去最深的根系。
大约是1993年夏,我五六岁光景。村东与西南岭上的几亩薄田,挂在向阳缓坡。歇晌时,祖父倚着田头碗口粗的黑松树坐下。他先从帆布包中取出老姥爷传下的紫砂壶,摩挲着壶身温润的包浆,沏上一壶酽茶。待茶汤在壶中转出琥珀色,他缓缓倾入粗陶杯中,热气裹着茶香与松针清气氤氲升起。祖父端起茶杯轻啜一口,眉宇间松快些许,这才掏出那杆磨得乌亮的铜烟袋……青蓝的烟雾升腾起来,带着辛辣的草木香,在他沟壑纵横的脸前缭绕、飘散,仿佛劳作后无声的叹息,与坡上的松涛融为一体。
秋冬之交,是大棚里种植蘑菇的时节。祖父在避风的洼地搭起暖棚,用山坡上耙来的黑松针铺就温床。他动作轻柔,好似在安放珍宝。棚内幽暗潮湿,弥漫着松针与泥土混合的、近乎神秘的芬芳。过些时日,便有小伞般的蘑菇怯生生钻出松软的土层,带着山林雨后的清气。这无声的萌发,是祖父向土地勤奋获取的另一种温柔馈赠,冬春时节,便成了乡邻餐桌上的鲜味佳肴。
2020年1月,吾儿降生,已是米寿之年的祖父升级当了曾祖父。儿子出生的第六天,一个腊月里寒冽的清晨,祖父独自一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老胶南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薛家岛。他裹着厚厚的棉袄,肩头还沾着霜粒。暖气充足的屋子里,祖父小心翼翼地接过襁褓中粉团似的重孙,脸上满是笑意。怀里的重孙正发出含糊的哼唧,小手无意识地抓挠他曾祖父脸上刀刻斧凿般的深纹。祖父笑得更灿烂了,舒展的皱纹如秋收后犁耙在黄土坡上留下的温软曲线,将我带回到四岁那年的一个雨天。
那天,祖父抱着我坐在老屋旁的树下,小刀在苹果上灵巧游走,果皮簌簌落下。雨点敲打阔叶的声响里,我用笨拙的小手往祖父那温热的铜烟锅里填压烟丝。他低头看我时,脸上犁出的,也是这般沟壑。
……
窗外,晨光越过小区里墨绿的雪松梢头,斜斜地照进屋内,将四代人的身影投映在光洁的地板上,浓淡不一,像一部无声的家族画卷。
在老屋院中,当我看到院中祖父栽种的娃娃菜伸展着嫩绿的叶片,茭瓜藤正沿着支架攀爬时,不禁豁然领悟——生命的藤蔓,原来在生死的两端同时扎下了深根!祖父走了,他一生俯首于这丘陵大地、肩挑日月的姿态,已如碑文镌进我的骨血。那些蘑菇清气、灶膛余温,那铜烟锅里残留的灰烬、紫砂壶壁上凝结的深色茶垢,连同他怀抱重孙时安然的笑纹,俱已化为我生命藤蔓最坚韧的纤维。原来,所谓“祖荫”,并非虚空投下的影子,而是这血脉如藤,在棕壤丘陵的厚土里生息不止,缠绕不休。
丘陵静默,唯有松涛如旧,那曾被祖父倚过的黑松,早已将根脉扎进岁月深处,比任何碑铭更接近永恒。
更多 往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