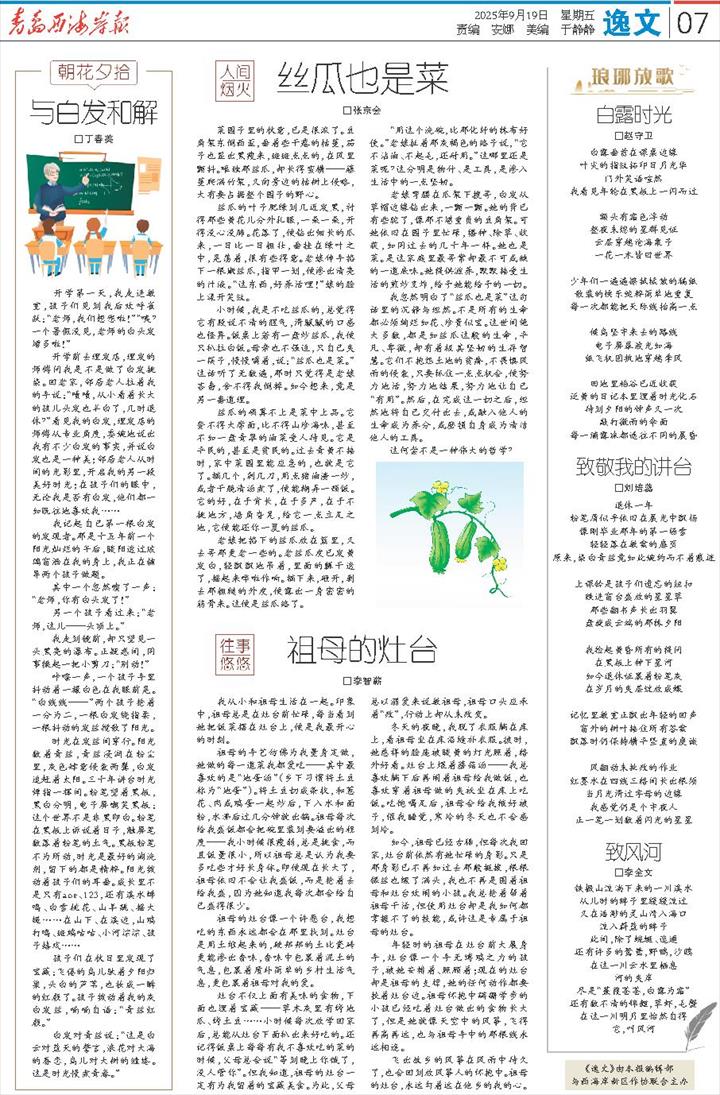文章内容
丝瓜也是菜
□张京会
菜园子里的秋意,已是很浓了。豆角架东倒西歪,垂着些干瘪的枯蔓,茄子也显出黑瘦来,斑斑点点的,在风里颤抖。唯独那丝瓜,却长得蛮横——藤蔓爬满竹架,又向旁边的枯树上侵略,大有要占据整个园子的野心。
丝瓜的叶子肥绿到几近发黑,衬得那些黄花儿分外扎眼,一朵一朵,开得没心没肺。花落了,便钻出细长的瓜来,一日比一日粗壮,垂挂在绿叶之中,晃荡着,很有些得意。老娘伸手掐下一根嫩丝瓜,指甲一划,便渗出清亮的汁液。“这东西,好养活哩!”娘的脸上漾开笑纹。
小时候,我是不吃丝瓜的,总觉得它有股说不清的腥气,滑腻腻的口感也怪异。饭桌上若有一盘炒丝瓜,我便只扒拉白饭。母亲也不强迫,只自己夹一筷子,慢慢嚼着,说:“丝瓜也是菜。”这话听了无数遍,那时只觉得是老娘吝啬,舍不得我倒掉。如今想来,竟是另一番道理。
丝瓜的确算不上是菜中上品。它登不得大席面,比不得山珍海味,甚至不如一盘青翠的油菜受人待见。它是平民的,甚至是贫民的。过去青黄不接时,家中菜园里能应急的,也就是它了。摘几个,剁几刀,用点猪油渣一炒,或者干脆清汤煮了,便能糊弄一顿饭。它的好,在于肯长,在于多产,在于不挑地方,墙角旮旯,给它一点立足之地,它便能还你一夏的丝瓜。
老娘把掐下的丝瓜放在篮里,又去寻那更老一些的。老丝瓜皮已发黄发白,轻飘飘地吊着,里面的瓤干透了,摇起来哗啦作响。摘下来,砸开,剥去那粗糙的外皮,便露出一身密密的筋骨来。这便是丝瓜络了。
“用这个洗碗,比那化纤的抹布好使。”老娘扯着那灰褐色的络子说,“它不沾油、不起毛,还耐用。”这哪里还是菜呢?这分明是物什、是工具,是渗入生活中的一点坚韧。
老娘弯腰在瓜架下搜寻,白发从草帽边缘钻出来,一颤一颤。她的背已有些驼了,像那不堪重负的豆角架。可她依旧在园子里忙碌,播种、除草、收获,如同过去的几十年一样。她也是菜。是这家庭里最寻常却最不可或缺的一道底味。她提供滋养,默默接受生活的煎炒烹炸,给予她能给予的一切。
我忽然明白了“丝瓜也是菜”这句话里的沉静与坦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必须绚烂如花、珍贵似宝。这世间绝大多数,都是如丝瓜这般的生命,平凡、卑微,却有着极其坚韧的生存智慧。它们不抱怨土地的贫瘠,不畏惧风雨的侵袭,只要抓住一点点机会,便努力地活,努力地结果,努力地让自己“有用”。然后,在完成这一切之后,坦然地将自己交付出去,或融入他人的生命成为养分,或磨损自身成为清洁他人的工具。
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哲学?
菜园子里的秋意,已是很浓了。豆角架东倒西歪,垂着些干瘪的枯蔓,茄子也显出黑瘦来,斑斑点点的,在风里颤抖。唯独那丝瓜,却长得蛮横——藤蔓爬满竹架,又向旁边的枯树上侵略,大有要占据整个园子的野心。
丝瓜的叶子肥绿到几近发黑,衬得那些黄花儿分外扎眼,一朵一朵,开得没心没肺。花落了,便钻出细长的瓜来,一日比一日粗壮,垂挂在绿叶之中,晃荡着,很有些得意。老娘伸手掐下一根嫩丝瓜,指甲一划,便渗出清亮的汁液。“这东西,好养活哩!”娘的脸上漾开笑纹。
小时候,我是不吃丝瓜的,总觉得它有股说不清的腥气,滑腻腻的口感也怪异。饭桌上若有一盘炒丝瓜,我便只扒拉白饭。母亲也不强迫,只自己夹一筷子,慢慢嚼着,说:“丝瓜也是菜。”这话听了无数遍,那时只觉得是老娘吝啬,舍不得我倒掉。如今想来,竟是另一番道理。
丝瓜的确算不上是菜中上品。它登不得大席面,比不得山珍海味,甚至不如一盘青翠的油菜受人待见。它是平民的,甚至是贫民的。过去青黄不接时,家中菜园里能应急的,也就是它了。摘几个,剁几刀,用点猪油渣一炒,或者干脆清汤煮了,便能糊弄一顿饭。它的好,在于肯长,在于多产,在于不挑地方,墙角旮旯,给它一点立足之地,它便能还你一夏的丝瓜。
老娘把掐下的丝瓜放在篮里,又去寻那更老一些的。老丝瓜皮已发黄发白,轻飘飘地吊着,里面的瓤干透了,摇起来哗啦作响。摘下来,砸开,剥去那粗糙的外皮,便露出一身密密的筋骨来。这便是丝瓜络了。
“用这个洗碗,比那化纤的抹布好使。”老娘扯着那灰褐色的络子说,“它不沾油、不起毛,还耐用。”这哪里还是菜呢?这分明是物什、是工具,是渗入生活中的一点坚韧。
老娘弯腰在瓜架下搜寻,白发从草帽边缘钻出来,一颤一颤。她的背已有些驼了,像那不堪重负的豆角架。可她依旧在园子里忙碌,播种、除草、收获,如同过去的几十年一样。她也是菜。是这家庭里最寻常却最不可或缺的一道底味。她提供滋养,默默接受生活的煎炒烹炸,给予她能给予的一切。
我忽然明白了“丝瓜也是菜”这句话里的沉静与坦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必须绚烂如花、珍贵似宝。这世间绝大多数,都是如丝瓜这般的生命,平凡、卑微,却有着极其坚韧的生存智慧。它们不抱怨土地的贫瘠,不畏惧风雨的侵袭,只要抓住一点点机会,便努力地活,努力地结果,努力地让自己“有用”。然后,在完成这一切之后,坦然地将自己交付出去,或融入他人的生命成为养分,或磨损自身成为清洁他人的工具。
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哲学?
更多 往期报纸